余光中:並未消逝的鄉愁
今天上午,朋友圈被一條來自台灣媒體的報道刷屏:著名詩人余光中在12月14日因病去世,享年89歲。看到這則報道時,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樣不期然地想起在中學語文課本上那篇流沙河的詩歌《就是那一隻蟋蟀》和他提到的「Y先生」,Y先生正是台灣詩人余光中。1982年,《星星》詩刊連續12期介紹「台灣詩人十二家」,3月號便刊登了余光中的詩與介紹文字。編輯流沙河為余光中回信中的那句話「在海外,夜間聽到蟋蟀叫,就會以為那是在四川鄉下聽到的那一隻」所觸動,很快寫下了那首詩。
詩人余光中(1928—2017)
最初的介紹里,余光中的那首短詩《鄉愁》最為出名。不難想像,在那個改革開放剛剛開啟,兩岸之間的文化與交流剛有鬆動的歷史時期,像「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這樣的句子,能撬動多大的歷史記憶與情感共鳴。
余光中《鄉愁》手跡
與1949年涉海而渡的許多台灣人一樣,余光中也屬於「大江大海」的一代人。祖籍福建永春的余光中,1928年生於江蘇省南京市。1948年,當他還在金陵大學外文系讀書時便開始寫詩,由於受到梁實秋的賞識,還出版了詩集處女作《舟子的悲歌》。1950年,隨父母赴台後,余光中繼續就讀於台大外文系,1953年,更與覃子豪、鐘鼎文等共創「藍星」詩社,成為台灣五六十年代異常活躍的現代詩人。
余光中的詩集處女作《舟子的悲歌》
儘管在大陸普通讀者的接受視野中,余光中一直有一個「鄉愁詩人」的身份,但是這種鄉愁,毋寧說更多出於一種傳統與文化的鄉愁。有人問起他大學時的專業選擇時,余光中曾經說:「我雖然讀的外文系,我不過是從西洋文學中學習,作為一種手段,目的還是把西方『冶金術』拿來,發掘東方的寶藏。」對於自由酷愛古典文學的余光中來說,對西方現代文學的學習,更多是一種「浪子回頭」式的借鑒。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現代主義的潮流席捲了台灣,從詩歌影響到散文、繪畫與音樂。余光中回憶起那個時期異常興盛的台灣詩壇:「在如何對待西化和傳統的問題上一時比較混亂,不僅詩人參與,社會人士也加入進來,因為各持主張,論爭很熱鬧。當時爭辯的主題大約有三個:文白之爭、現代畫、現代詩。而現代詩則是論辯的重點。在古典詩與『五四』的新詩之後,現代詩的產生是『必然』,再走回去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現代詩畢竟是新生的藝術,毛病在所難免。那麼現代詩究竟該怎樣寫,它對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潮流該持怎樣的態度?」
在那種熱烈的討論氛圍中,余光中嘗試了一系列現代主義的詩歌創作。可是不久,他開始警覺西化之失,並向一些西化作家直言苦諫,毅然告別虛無與晦澀,回歸傳統,寫下許多諸如《尋李白》等一系列以古人為題的人物詩,以及像《白玉苦瓜》等博物館文物為題的古意斑斕的詩歌。然而,在余光中看來,這時的回歸傳統,已是融合了現代精神的「中國詩的現代化」。
余光中與妻子范我存
也許正因為有這樣的認識,儘管從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余光中曾經三次留學或任教於美國,還學會了開車,喜歡上了披頭士樂隊,但縈繞在他詩歌中的主題依然是揮之不去的鄉愁。在一次訪談中,余光中說:「迄今我成詩千首,鄉愁之作大約佔其十分之一。與此相近之作尚有懷古、詠物、人物等主題,數量亦多。在鄉情之外,我寫得很深入的主題還包括親情、友情、愛情、自述、造化各項。因此強調我是『鄉愁詩人』,雖然也是美名,卻仍不免窄化了我。」
更重要的是,余光中理解中的鄉愁,內涵廣闊,不僅包含地理意義、家鄉風土、歷史在內的文化印記,還有格局大小之別。舉例來說,「『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小而親切;『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大而慷慨。」
「新古典主義」詩學的大陸影響
1992年,余光中第一次回到大陸。但他的詩歌,早已先於人而抵達。「朦朧詩」的代表詩人楊煉,對我回憶道,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自己詩歌的英文譯者便送給他一本余光中翻譯的《英美現代詩選》,其中對於葉芝、龐德等人的翻譯,令他印象深刻,至今還將其保存在柏林的家中。
「余光中的詩歌對音樂性非常講究,比較有名的《鄉愁》,很強調音樂性,講究押韻,與古典詩歌的關係很密切。」儘管楊煉認為余光中與古典詩歌的銜接方式比較簡單,與自己的寫作沒有太大關係,但在他看來,在1980年代中期,大陸詩歌局面初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余光中的影響很大。原因在於,「他的詩第一非常中文、非常中國,第二朗朗上口很悅耳,第三又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詩歌。所以對當時一批抒情詩人影響很大,這些詩人的寫作介乎於官方詩人與朦朧詩帶來的現代氣息之間,所謂港台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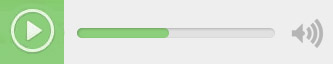 詩人王家新也很早就讀過余光中的詩集《白玉苦瓜》,在他看來,後者對大陸詩歌的影響主要在1980年代。余光中早年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洗禮,後來致力於發掘與整合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和新詩的藝術經驗,這種浸透語言與文化鄉愁的「新古典主義」詩歌寫作,無疑給漢語詩歌帶來一種新的可能。王家新舉了詩人張棗的例子:「他確實讓當時許多一心執迷現代主義的年輕詩人重新發現了古典,並意識到可把中國古典引入現代。雖然台灣詩壇的復古風很有問題,但離開它們的影響和啟發,據很難有《鏡中》這樣的詩出現。」
詩人王家新也很早就讀過余光中的詩集《白玉苦瓜》,在他看來,後者對大陸詩歌的影響主要在1980年代。余光中早年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洗禮,後來致力於發掘與整合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和新詩的藝術經驗,這種浸透語言與文化鄉愁的「新古典主義」詩歌寫作,無疑給漢語詩歌帶來一種新的可能。王家新舉了詩人張棗的例子:「他確實讓當時許多一心執迷現代主義的年輕詩人重新發現了古典,並意識到可把中國古典引入現代。雖然台灣詩壇的復古風很有問題,但離開它們的影響和啟發,據很難有《鏡中》這樣的詩出現。」
王家新儘管沒有對余光中「新古典主義」詩學的問題更多展開,但毫無疑問,類似的質疑也曾出現在台灣詩壇。1986年元旦,余光中在他的第8本詩集《敲打樂》的新版序言中寫道:「有些論者一直到現在還在說,我的詩風是循新古典主義,與現實脫節云云。什麼才是現實呢?詩人必須寫實嗎?詩人處理的現實,就是記者報導的現實嗎?這些都是尚待解答的問題。不錯,我曾經提倡過所謂新古典主義,以為回歸傳統的一個途徑。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認為新古典主義是唯一的途徑,更不能說我目前仍在追求這種詩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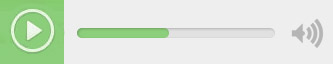
可見,無論是鄉愁也好,新古典主義也好,都不足以概括余光中本身徘徊遊走於中文與英文、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詩歌創作。況且,在余光中心目中,詩歌只是他生命的一個維度,詩歌、散文、評論、翻譯合起來才構成他創作完整的四維空間。
據說,梁實秋曾稱讚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無獨有偶,在詩人楊煉看來,余光中的散文成就要比詩歌高,而他的翻譯在當代中文詩人中更是突出:「比如葉芝的《麗達與天鵝》,他對外語詩意與形式吃得非常透,並把這種感受和對詩的要求融化到翻譯中,進入化境,絲毫沒有現代白話文的生澀之感。龐德的那首《理查王》,更難翻譯,非常嚴格的詩歌形式,但同時第一人稱寫作的理查王說的語言非常粗俗,他可以把這種粗俗的語言,與非常嚴格的韻和形式結合得完美無缺,甚至有點炫技的感覺,但這種炫技在詩歌意義上非常高級。」
2006年,我曾在北京大學校園裡目睹過余光中詩歌講座的空前盛況。一間最多容納三四百人的教室里擁入近千人,聽講的學生甚至站到了講台兩側。那時的我還頗為意氣,在我看來,這種明星式的圍觀完全與詩歌無關,憤憤之下甚至擠出了教室。
後來想想,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如同今日對詩人的紀念,擁擠熱鬧之中,有人真正關注他的詩歌就好。對於這一點,余光中向來自信,1983年,在詩集《白玉苦瓜》10版的自序中他寫道:「安迪·沃霍說:在大眾傳播的現代社會,每人輪流出名五分鐘。流行的東西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傷,就是既快又高的折舊率。詩,從來不是什麼流行的東西,所以也沒有什麼折舊率的問題。對於屈原或杜甫,折舊率似乎毫無作用。」
推薦閱讀:
※余光中的詩,不入流!
※汪國真和余光中的去世,人們表現得為何如此不一樣?
※余光中:《當我死時》
※余光中紀念專題
※「女兒奴」余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