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布盧默|莫扎特的風格與影響(上)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莫扎特的風格與影響(上)
[德]弗里德里希·布盧默 著
Jacqueline 譯
【譯者按】本文譯自《莫扎特指南》(The Mozart Companion,Rockliff,1956),原題Mozart"s Style and Influence,英譯者H.C.Stevens。作者布盧默(Friedrich Blume,1893~1975),德國音樂學家,長年從事古樂編訂工作,著述豐富,領導編纂了14卷百科全書《歷史的與現時的音樂》(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是研究巴赫與莫扎特的權威。文章論及古典風格,論及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的風格比較,論及莫扎特的晚期風格,論及莫扎特對浪漫主義者的影響,多有妙語;在具體作品的分析方面,往往著墨不多而一語中的。對古典及古典以前音樂風格的全面認識始於二十世紀,其中有作曲家的工作,也有音樂學者的工作。近五十年來音樂學又有了很多進展,就本文論及的問題而言,風格方面有Charles Rosen的《古典風格——海頓、莫扎特、貝多芬》和《奏鳴曲式》,影響方面有Daniel Heartz的《海頓、莫扎特與維也納樂派,1740-1780》等。
1785年2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三首弦樂四重奏「新作」在莫扎特家中上演,此時利奧波德·莫扎特正在維也納的兒子兒媳這裡。今天我們知道這是題獻給約瑟夫·海頓的六首四重奏中的後三首(K.458,464,465,作於1784年11月和1785年1月間)。當時這六首四重奏尚未題獻給海頓:Artaria印行的初版上,獻辭的日期是1785年9月1日。海頓本人也出席了莫扎特家中的這場演出,不過他之前便已聽過這些作品:1785年1月22日利奧波德從薩爾茨堡給在聖吉爾根的女兒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沃爾夫岡說起「上星期六他為他親愛的朋友海頓和別的好朋友演奏了六首四重奏,而且把它們賣給Artaria出版社,得了一百個達克特」。莫扎特在獻辭里提到的時間很可能是指這個晚上,即1785年1月的早些時候:「我親愛的朋友,正是您,前次於首都小住期間,向我表達了您的欣喜之情。您的讚許鼓勵我……」正是這一天,1785年2月12日,利奧波德·莫扎特和約瑟夫·海頓作客沃爾夫岡家中聽到這三首四重奏(利奧波德認為它們比前三首「在某種程度上容易一些,但同時又都是傑作」),海頓轉向老莫扎特,道出日後有名的一段話:「我要在上帝面前以一個誠實人的身份對您說,您的兒子是我以個人結識及以聲名知曉的作曲家中最偉大的一位。他有品味,更有深具洞察的作曲智識。」利奧波德在1785年2月14/16日寫給女兒的一封信里提起此事,以他自己簡捷而自信的方式轉述了海頓的評價,雖未受寵若驚,得意之情卻溢於言表。當時海頓已是歐洲名聲最為顯赫的音樂家,此番話一言九鼎,是那個時代沃爾夫岡所能獲得的最高評價。莫扎特在獻辭中稱海頓為「德高望重的人」,絕非客套說辭。他寫道「我的六個孩子是長時間艱苦勞作的果實」,而又補充說海頓的讚許鼓勵他將六首四重奏置於海頓的保護之下,這正是2月12日海頓評語的迴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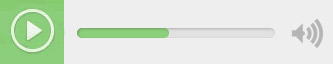
莫扎特:C大調弦樂四重奏K.465「不協和音」,第一樂章 柔板 - 快板,演奏:布達佩斯弦樂四重奏組。
與當時音樂家中流行的諂媚吹捧不同,海頓將自己的評價蘊於簡練的言詞中。眾所周知,他後來一再表達了對莫扎特的高度評價——有一次是在維也納對《堂璜》的大爭論期間,而最有說服力的或許是他1787年致布拉格劇院經理Roth的信函:
「假如我能說服每一個音樂愛好者,特別是那些身居高位者,讓他們確信莫扎特的音樂不可模仿;假如他們象我一樣,具有嚴肅的音樂理解方面的判斷力;假如他們象我一樣,讓他的音樂觸到自己的靈魂——假如是這樣,各個國家就會爭著要把這件珍寶留在自己的領地……讓我忿忿不平的是,竟然沒有一個帝國或皇室的宮廷為這位獨一無二的莫扎特提供職位。請原諒我發了脾氣;我太愛惜此人。」
利奧波德·莫扎特和海頓的這些話都不是出於溺愛而言過其實。他們都是在音樂感受方面有判斷力的人,決不說不負責任的話。海頓的判斷對後世有更大的意義,因為眾所周知,莫扎特在維也納的十年里,他的價值遠遠沒有得到廣泛的承認。雖然他的每次音樂會或歌劇演出都會立即得到承認,但這種承認卻被主流的批評意見淹沒(這些批評我們現在還能讀到),他的作品在出版商那裡的失敗毫無疑問地印證了這一點。在當時,如果作品不能取悅音樂出版商,那一定是之前面對公眾時遭到了失敗;如果公眾有需求,一定會有出版商印行。1800年貝多芬可以自豪地說:
「我的作品給我帶來了一大筆收入,我敢說我接到的委託比我能寫的還多,這讓我很高興。我寫的每一件作品會有六七個甚至更多的出版商來要;我不再需要討價還價,我出價,他們給錢。」(致Wegeler,1800年6月29日)
海頓對自己的作品或許也可以說同樣的話。那個年代在出版界的成功是衡量藝術影響的可靠判據。海頓的話「假如我能……」以及「讓我忿忿不平的是……」顯然也表明他想做點什麼來糾正人們的偏見,改變莫扎特的作品不受公眾承認的局面。

不過,有確切的證據表明早先莫扎特的音樂曾得到過極高的評價,比如1783年3月內弗【Christian Gottlob Neefe(1748-98),德國音樂家,在波恩教過貝多芬——譯註】在Cramer的《音樂雜誌》(Magazin für Musik)上寫了一則廣告,介紹新出版的貝多芬據E. Chr. Dressler的進行曲所寫的九個變奏,其中寫道:「這位年青的天才[貝多芬]如果持續這樣的進步,一定會成為第二個沃爾夫岡·阿瑪多伊斯·莫扎特……」請注意,那時內弗不大可能熟悉莫扎特的多數作品,他不大可能見過莫扎特本人,他本人來自Doles和J.A.希勒【Johann Adam Hiller(1728-1804),德國作曲家,被認為是歌唱劇(Singspeil)的創始人——譯註】的略顯老派的撒克遜樂派,我們甚至無法想像他怎麼會看到音樂中那種人性的天才(權且這樣說),不是海頓的而是莫扎特的未被賞識的天才。看來莫扎特的音樂唯獨在波恩得到了理解;這一點在後來貝多芬的書信集里找到了印證,1792年10月29日斐迪南·華爾斯坦伯爵【Ferdinand Waldstein(1762-1823),貝多芬的保護人——譯註】致貝多芬:
「莫扎特的天才仍在為它托生的身體的逝去而哀傷和哭泣。在思如泉湧的海頓身上它只是找到了暫時的寄所而非最後的歸宿;它渴望與另一個人相結合。經過不懈的努力,你定將從海頓的手裡接過莫扎特的精神。」
這段有名的話出自一位純粹為音樂所感染的業餘涉獵者筆下,此時莫扎特去世僅一年;對三位作曲家海頓、莫扎特、貝多芬之間的關係,這實在是一段精彩的評論。

莫扎特對同時代人產生的影響,目前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研究結果。當然,這種影響不能和海頓的全面成功相比。莫扎特家人和朋友的小圈子裡的熱衷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只要離開他們到了那些樂評家和愛好者的大圈子裡,就會看到太多不利的評價。諸如Nageli和科策盧【Leopold Kozeluh (1747-1818),捷克作曲家,曾在布拉格繼任莫扎特的職位——譯註】這樣的音樂家,以及Grassalkowics伯爵甚至奧皇約瑟夫二世這樣的愛好者,作出的都是些懷疑的、保留的甚至是負面的評價。當莫扎特「最得意的學生」(Kelly語)托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1765-1838),英國作曲家、管風琴家——譯註】和朋友一起把題獻給海頓的六首四重奏送到那不勒斯的G.G.Ferrari那裡時,發現不得不提醒他防備直接被拒之門外的打擊。在1798年的《沃爾夫岡·神愛·莫扎特樂長生平》(Leben des K.K.Kapellmeisters Wolfgang Gottlieb Mozart)一書中,Niemtschek說到這種反對意見經常出現:「莫扎特的作品太難,太挑剔,藝術成分太重,耳朵根本沒法承受。」他試圖為莫扎特辯白:「他作品中的難點並非刻意為之,而不過是天才偉大原創性的自然結果。」在佛羅倫薩,九次排演失敗之後,《堂璜》的第一幕被扔到一邊,因為它「無法演出」。據說出版商Hoffmeister對莫扎特說:「用通俗一點的風格來寫,不然我沒法給你出版,一個錢也沒法給你。」而莫扎特答道:「那我就一個錢也不掙好了,我寧可餓著肚子去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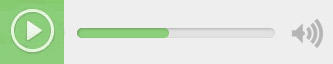
莫扎特:歌劇《唐璜》K.527序曲,演奏:Carlo Maria Giullini指揮愛樂樂團。
關於莫扎特本人的生活圖景我們並不了解。從奇蹟般的神童一躍成長為米蘭歌劇院滿場喝彩的大師,隨後就經歷了「狂飆突進」式的曼海姆-巴黎插曲【指1778年曼海姆-巴黎之行途中喪母與失戀——譯註】,此時的莫扎特在與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衝突中表露著自己——這外部世界中除了成功什麼都有。在返鄉後不久他就與舊制度決裂,與音樂家的傳統生活方式決裂,試圖在藝術和社會地位兩方面掙脫束縛。而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在維也納,在自己選擇的「藝術家」(在這個詞的浪漫主義的意義上)的孤獨中,莫扎特獻身創作,同時也日漸與世隔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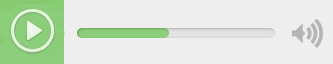
莫扎特:歌劇《費加羅的婚禮》K.492序曲,演奏:Erich Kleiber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
莫扎特唯一在生前廣為演出並獲得決定性成功的歌劇是《後宮誘逃》。在他去世後《魔笛》迅速征服了歐洲的舞台;《堂璜》與《費加羅》稍晚,而《女人心》則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被人們接受。【《狄托的仁慈》更受公眾歡迎,歌德讓著名的Lauchstedt劇場以該劇的上演揭幕——原注】莫扎特大部分器樂作品是通過André的版本廣為人知的,也就是說大約在1800年,相比之下生前只出版了極少的作品。有些作品以抄本流傳,但也只是少數,而且主要是管弦樂作品。
毫不誇張地說,與約瑟夫·海頓相比,與迪特斯多夫【Karl Ditters von Dittersdorf(1739-99),奧地利作曲家——譯註】、科策盧、Vanhal(Wanhal)、克萊門蒂以及幾十位不那麼重要的作曲家相比,莫扎特生前甚至並未被公認為作曲家。直到年青一代的浪漫主義者登台,莫扎特方獲成功,這代人相信自己在莫扎特身上找到了精神上的親緣。於是莫扎特不可理喻的、明暗交融的一面,雖然只是他個性的一個側面,現在就可以強有力地表現出來;這也解釋了莫扎特被推遲的、然而卻是持續的和不斷增長的成功。浪漫主義時期的美學家與詩人,比如Wackenroder和蒂克,A.W.施萊格爾和E.T.A.霍夫曼,把莫扎特當成了偶像。《魔笛》不但觸動歌德寫出續作(《魔笛》第二部,斷章),也影響到施萊格爾的《榮譽門與凱旋門》(Ehrenpforte und Triumphbogen für den Theater-Pra"sidenten von Kotzebue bey seiner gehofften Rückkehr ins Vaterland,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800)、蒂克的《穿靴子的貓》(Gestiefelter Kater)和格里爾帕策的《幻夢人生》(Der Traum ein Leben),更不用說由它衍生的一大堆歌劇仿作。《堂璜》的聲音迴響在霍夫曼的著名小說《塞拉皮翁兄弟》(Serapionsbrüder)和《雄貓穆爾的生活觀》(Kater Murr)中,迴響在克萊斯勒樂長身上;他的小說處處迴響著莫扎特的聲音,而這迴響隨後又傳給了羅伯特·舒曼。【舒曼的《克萊斯勒偶記》(Kreisleriana)即受霍夫曼筆下克萊斯勒樂長的啟發而作——譯註】瓦格納對莫扎特的狂熱也是在同一塊土壤上培養起來的。即使在這時莫扎特基本上也還是藝術誤解的犧牲品:他的藝術屈於浪漫主義的臆想之下。浪漫主義藝術家在莫扎特身上感受到偉大的愛,在貝多芬身上感受到熾熱的激情;但對於海頓,他只能報以寬容的一笑。當然也不應忽視另外一些人:詩人讓·保爾,比莫扎特小七歲,音樂家C.F.策爾特【Carl Friedrich Zelter(1758-1832),德國作曲家、指揮家、教師,與門德爾松合作復興巴赫作品——譯註】,比莫扎特小兩歲,他們看到海頓遠比莫扎特更能實現他們的理想;特別有意味的是,在致歌德的一封信里,策爾特試圖通過與巴赫相比來概括莫扎特:
「莫扎特比之於巴赫,猶如尼德蘭諸大師比之於義大利和古希臘藝術家,我是在逐步認識到這件事以後,才開始對二者都給予極高的敬重,而不再向其中一位提出只有另一位才能達到的要求。」
早在維也納古典時期,對作曲家價值高低的衡量就已經完全取決於他在大大小小的音樂圈子中留下的第一印象。從前,對音樂的評價與其說是藝術的不如說是科學的,對音樂家的評價更多的是基於他們的學識而非他們對同時代人的影響,而這樣的日子已經成為過去。評判的權力漸漸從樂評家手上轉到愛好者手上,轉到公眾音樂會的廣大聽眾手上。與此同時,聲樂的支配地位為器樂所取代(歌劇是唯一的例外)。作曲家要想贏得聽眾,就面臨這樣一項任務,他必須運用器樂的語言來影響廣大音樂愛好者,把他們從歌劇舞台周圍吸引過來,而這些聽眾已經不能再按地位、等級、信仰和教育水平作出區分,甚至不能按國籍和母語作出區分。海頓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我的語言全世界都能理解」,這句話應該完全按字面意思來理解:這種語言可以說給所有的人聽,無論其國籍、生活環境和信仰如何。海頓《創世紀》的演出引來數千人的朝聖隊伍,首席執政官【指拿破崙——譯註】以海頓本人能夠親臨此曲在巴黎的首演為榮。關於莫扎特的《魔笛》,歌德的母親這樣寫道:「沒看過它的人簡直會覺得臉上無光。就連那些手藝人、園丁和鄉下佬,因為他們的小孩在戲裡扮演猿人和獅子,也都要去看呢。從來沒見過這麼熱鬧的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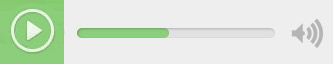
莫扎特:歌劇《魔笛》K.620序曲及第一幕第一部分,卡拉揚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
這或許是已知的音樂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場變革。一千年以來音樂家總是安身於社會等級和心智秩序的一個指定位置上;他有些規定的任務要演出,作品必須滿足要求,嚴格為慣例所約束,而這些要求和慣例是由特定的社會階層或是由贊助人來制訂的。他的工作範圍局限於宮廷慶典、宗教儀式、市政典禮以及市民公共生活中的種種其他場合。每一作品都有其指定的場合和指定的受眾群體。而要寫出「面向所有人的音樂」,無論面對的是公爵還是男僕,貴婦還是民女,英格蘭人還是義大利人;要寫出既高度精鍊又易於通俗化的音樂,就成為一項前所未有的新任務。成熟時期維也納古典風格的最高成就,或許就在於它面對這一任務時的純熟自如。作曲家可以創造新的「心靈的語言」,雖然它同時也是「人性的語言」,但卻完全發自他自己的內心世界。之前的所有音樂,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必須嚴格地約束在傳統的框架內。而海頓的弦樂四重奏和交響曲,無論是語言、形式還是內容都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作曲家不再需要為教會、市政廳或王公貴族的沙龍創作(雖然他還會經常收到來自這些地方的委託);不再為教儀、慶典、舞會或宴飲創作,而要為公眾音樂會,為音樂的消費者創作;對出版商來說情況也是一樣。這場曠日持久的變革始於十八世紀下半葉,甚至到二十世紀仍未結束;無線電廣播和錄音技術的發展只是把它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並未改變它的實質。這場變革讓音樂家擺脫了先前社會地位和指派任務的束縛,與此同時也迫使他走向獨立。它把希臘人的禮物「藝術上的自由」贈與音樂家,與此同時也終結了作曲家恪守天職循用慣有曲式和作曲法的古老傳統;作曲家業已改變的社會功能不容置疑地要求他的作品必須是「原創的」。海頓以遵循慣例的、不動感情的洞察力理解了這一變化——「所以我必須做原創的東西」。他開始堅定地、富有邏輯地著手於音樂的新任務,從而贏得了同時代人的愛戴和高度評價。莫扎特與傳統決裂,從而被毀掉了:在他最偉大的成熟時期的十年里,藝術上的誤解與物質上的匱乏始終伴隨著他。而在這方面,貝多芬繼承了一筆財產;他君臨於旁人之上,對他們十分暴虐:「他們不能再跟我討價還價了;我出價……」

三大師在同時代人那裡所獲得的截然不同的評價,他們的風格所呈現出的高度多樣性,都是基於這樣的歷史事實之上。這種多樣性的程度遠遠高於此前的歷代大師。這種多樣性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彼此之間的年代差異,因為對我們來說,巴赫或許茨時代的德意志風格,以及佩爾戈萊西或蒙特威爾第時代的義大利風格,似乎要比維也納古典大師的風格更加統一。當然,用具體的詞語來表述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之間的風格差異,或者確切地定義莫扎特的風格如何不同於另兩位大師,都是極為困難的。有的差別很明顯:貝多芬鋼琴奏鳴曲Op.10,No.3(c.1797)的廣板主題絕不可能出自海頓或莫扎特筆下;海頓最後一部交響曲(No.104,1795)的行板主題絕不可能出自莫扎特或貝多芬筆下;莫扎特單簧管協奏曲(K.622,1791)的柔板主題絕不可能出自海頓或貝多芬筆下;這裡說的都是一些顯而易見的情況。但差別究竟在何處呢?當然有一些邊界的情形:貝多芬早期的管樂作品(八重奏,Op.103;三重奏,Op.87;六重奏,Op.71;五重奏,Op.16;小夜曲,Op.25;七重奏,Op.20,年代都是1792~1800)當中有很多非常接近莫扎特的因素;海頓的一組弦樂四重奏Op.50(1787)明顯可以看出年長的作曲家已經熟悉了那位年青的同代人題獻給他的四重奏作品。不過,主題上的相似性一般不會發展到讓人分不清作者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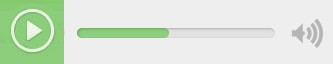
莫扎特: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K.622,第二樂章 柔板,演奏:Richard Stoltzman(單簧管)、英國室內樂團。
要確切地指出這些差別,一大難點在於那個時代的作曲家使用的外部曲式是相似的,無論是大麴式還是小曲式。奏鳴曲式實際上從未被當作絕對標準,雖然音樂文獻常常錯誤地堅持這一點;它一直是靈活的,應用於各別情形時總是變化多端。在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Opp.2~10中,它嚴格服從於一個統一標準,然而貝多芬自己從Op.14開始打破了這個標準,並走得越來越遠。在莫扎特和海頓的鋼琴奏鳴曲里,奏鳴曲式的布局從沒有過什麼固定的格式。海頓在交響曲中構建了自己的奏鳴曲式布局,以至於通常不用第二主題。海頓將這一布局廣泛地應用在他最後的全部二十到二十五部交響曲當中。貝多芬的前兩部交響曲承襲了海頓的曲式,莫扎特的最後三部交響曲則與之相去甚遠。而在「抒情」樂章(慢樂章)中,在小步舞曲或諧謔曲中,在迴旋曲(終曲)中,曲式的變化甚至比奏鳴曲式更為普遍。在最一般的層次上,三大師的作品共用同一布局,而在此一般層次之下他們則自由發揮。這種態度也體現於其他的嚴格曲式:莫扎特的協奏曲和貝多芬早期的協奏曲(這一體裁基本上可以不談海頓),第一樂章的一般布局可以縮減為一個簡單公式:四段全奏加三段獨奏,中間一段獨奏很長,第三段獨奏後加一個華彩段。但是在每個細節上,在調性的安排和主題的組織上,還有其他方面,這一布局總是服從於無窮的變化,在莫扎特筆下尤其如此。就曲式而言,也許是在弦樂四重奏中,三大師表現出了最多的相似性:海頓的Op.20(1772)和Op.33(1781)建立了範本,而
從莫扎特的D小調四重奏K.173(1773),到貝多芬的一組四重奏Op.18(1798~1800),猶如以海頓的範本作成的卡農。即使在這裡,細節上的變化也是很多的。獨特的作品之所以成為獨特的,是因為蘊藏其中的個性與表現手法是獨特的。聲樂的領域也有同樣的情況:諸如歌劇詠嘆調的布局或彌撒曲中不同唱段的布局是共同的;但作品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沒有哪個作曲家會只用一張藍圖寫所有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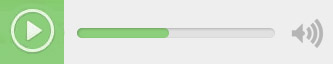
莫扎特:D小調弦樂四重奏K.173,第一樂章(快板但非常有節制),演奏:Talich Quartet。
莫扎特不同樂章的曲式靈活多變,富有彈性,因而要從中歸納出莫扎特的個人風格,必將徒勞無功。曲式總是取決於具體實現的情況,排除了任何概括性縮減的可能。此外,我們在確定莫扎特的風格方面還會遇到另一困難。他的早期作品,比如作於羅馬的三部交響曲K.81,97,95(73l-n),或弦樂四重奏K.80(73f),也許還包括1769年和1771年住在薩爾茨堡期間所作的宗教音樂,都是嚴格根據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樣板改寫而成的,所以我們沒有什麼確定無疑的方法從中辨別他的個人風格。注意到這一點,自然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我們到底能把什麼描述為莫扎特的風格?他的音樂里真的有什麼東西可以看成一種統一的「莫扎特風格」嗎?他的哪些作品可以認為是他的人格以音樂的語言作出的最終表現呢?
(未完待續)
和 鳴 記
宜言飲酒
推薦閱讀:
※服裝設計的風格分類
※家裝中的【美式田園風格】傢具
※田園風格
※小編為大家帶來了歐式風格的一些裝修技巧
※設計讓樓梯華麗轉身,18款複式樓現代簡約風格樓梯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