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潘蛟:《流動社會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組織與群體行為研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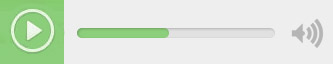
潘蛟(傑潘克古),彝族, 四川涼山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代表作: 《火把節紀事:當地人觀點?》、《族群及相關概念在西方的流變》、《解構中國少數民族:去東方學化還是再東方學化》、《民族國家與民族問題》等。研究方向: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社會分層、族群認同、西南少數民族研究。
半年多前就答應了劉東旭寫這個序言,拖到今天,延遲此書的出版,實在是抱歉!
拖沓的原因當然是課多,雜務分心,但也是因為從來沒有給別人寫過序,不知道該怎樣寫。但是,這序又是需要寫的。因為東旭是我指導的研究生,這書是由他博士論文改成,而且還算是我所申報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1AMZ007),新增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重大項目(MUC2011ZDKT1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劉東旭本科畢業於中山大學人類學系,2007年進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成為我指導的碩士研究生。他碩士論文研究的是他家鄉貴州湄潭縣宗教寺廟的復興、信眾的自組織等問題。他的發現是,在信眾的自組織活動中,女性信眾尤為活躍,起著引領和骨幹作用,男性則主要是為她們提供一些宗教儀規方面的知識和技術上的服務。對此,他的解釋是:在當地的文化中,女性的身份以及生命意義歸屬是依附於夫家的,這對那些喪夫、喪子,或經歷了婚姻離異的婦女會生成某種生命意義危機,而皈依宗教則能幫助她們進入另一種意義體系,從這危機中解脫出來。顯然,這解釋牽涉到儒、釋、道等不同信仰體系之間的關係,以及信仰體系多元對於生命實踐的意義等諸多問題。這碩士論文在答辯會上得到一致好評,在場的何其敏教授更是厚愛有加,讓他把這論文壓縮出來,由她推薦到了刊物上發表。
獲得碩士學位後,東旭繼續跟著我攻讀博士學位。起初,想讓他接著做宗教研究,繼續探討性別與宗教的關係,以及信仰體系多元對於中國人生命實踐的意義等問題。但他有一些猶豫,他更希望在家鄉之外找到一個新研究領域來做自己的博士論文。不久我從國家社科基金等處申請到了研究經費,做中國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研究,缺人手,也就把自己的學生們引到了這個方向上來。我們的調研是從聚集在東莞工廠里做工的涼山彝人開始的。2010年我送了四個碩士研究生去東莞謝崗鎮做田野工作,後來其中三人的碩士學位論文寫了彝族農民工,另一人寫的則是當地一個村莊地權和經濟再集體化問題。東旭的博士論文選題大致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確定的。自這以後,他與東莞的彝族工頭們建立了不錯的關係,不斷往返於東莞—涼山—北京之間,對於東莞彝族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形成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潘蛟教授帶弟子在珠三角考察
記得也就是這一年,東旭和同學宋宇曾會同20多位彝族農民工被彝族工頭送到富士康的一家工廠里做工。有意思的是,這些彝族工人第二天就抱怨這工廠工作太累,要求工頭把他們調換到其他工廠去。工頭拿這些工人沒辦法,只好認倒霉,趕緊把他們調換到了另一家工廠去。東旭和宋宇當然可以跟著這幫工人一起被調換,但是他們選擇了留下,直到做滿一個月,拿到工資為止。從這個事件看,這些彝族工人與工頭的關係似乎並不像那些新聞媒體報道的那樣簡單:「經濟強制的人身依附關係」——涼山彝族奴隸制的殘餘。
彝族農民工與彝族工頭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究竟應該怎樣看待珠江三角洲的這種彝族「領工制」?東旭的研究表明,這種領工制實際上是從主流社會認可的勞務派遣制蛻變而來,差異不過在於:除了經濟上的契約關係之外,它還倚重親戚,同鄉和族群等社會網路關係。它和那些勞務派遣公司的區別主要在於,它沒有明確的註冊資本,沒有向國家註冊和交稅。而就今日情況看,不少具備了資本條件的彝族工頭事實上也已註冊了自己勞務公司,變成了合法的勞務派遣經紀人。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領工制條件下,投身於彝族工頭麾下的農民工除了涼山彝人之外,也還有白族、傈僳族、甚至漢族人,等。其中的原因大致是:跟彝人工頭更省心,有人罩著,有工做,不用擔心工廠欠薪,廠主跑路,以及工傷索賠,而且跟隨勞務派遣公司的實際成本未必就比跟隨彝族工頭低,等等。簡言之,彝族領工制的湧現實際上是適應了珠三角企業為降低成本竭力規避社會責任,國家勞動合同法貫徹落實程度低,工會組織有名無實,農民權益難以得到切實保障的場景。在這個意義上,彝族領工制更像是一種「准工會制」或「准勞務派遣制」。認為農民對於城市和工廠的適應必定是一個去人情關係化,被原子化為六親不認的理性個體的進程,否則,他們的問題就是對於城市化和工人工資化的不適應,這不過是齊美爾、路易·沃斯(Louis Worth)等人在20世紀前期對於現代城市性的意識形態構建而已。事實表明,基於情緣、鄉緣、族源的社會紐帶在任何社會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在移民對於陌生社會的適應過程中更是如此。東旭的研究表明,彝族農民工事實上是在根據他們的自身條件積極適應珠三角的用工需求和制度安排,這個過程既有路徑上的依賴,也有傳統的發明和創新。就他們的自身條件和面對珠三角場景而論,領工制的湧現和家支活動的再組織是具有一定適應性的,而真正不太適應當下勞動力流動的反倒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城市制度和民族政策安排,等等。
東旭在東莞的田野調查實際上很受當地國保部門關注,他們曾經常通過東旭來問詢這些彝族農民工的情況,並多次告誡東旭注意人身安全。彝族農民工在東莞的口碑是極差的,常聽到的抱怨是:不講衛生,酗酒鬧事,經常借工傷、欠薪等事呼朋引類,敲詐廠主,不僅不把當地黑社會放在眼裡,而且連聯防隊和警察都敢打,等等。據說事後有不少廠主發誓今後不再使用彝族農民工,甚至有廠主哭述使用彝族農民工是因為自己沒有能力去僱傭更「優質的勞力」,等等。事實上,東莞當局也是不太鼓勵使用彝族農民工的。據說但凡工廠使用了五個以上的彝族農民工,就需要向當地公安報備,等等。既然如此,當地怎麼還會有那麼多的彝族農民工呢?東旭的回答大概是:在珠三角的勞動力市場上,這些彝族農民工的區位是「後備」,中國製造的發達需要有一支常備不懈的勞動力後備軍。
與彝族農民工相處真是不安全?東旭自己好像沒有這樣的感受。那麼,這些彝族農民工為啥會被當做不安全的人群呢?所謂「安全」在這裡指的究竟是什麼?想去想來,我以為大概是指這些人的群聚性及與此相關的抗爭性。他們動輒群聚圍廠討薪、索賠,反抗甚或報復對於他們的歧視,不太習慣於按「合法的程序」解決問題。然而,所謂的「合法程序」在珠三角的特殊場景中真是那麼有效嗎?我看未必。我曾遇到過這樣一個案例:一家勞務公司送了一批學生工去一家工廠做工,在該發工資的時候,工廠的老闆不見了。這家工廠的產權屬於該廠所在的村委會,但工廠很早就被出租給一個香港人。而這香港人後來又把這廠轉租給了一個湖南人。這湖南人正是欠薪跑路的老闆。由於這事的責任關係較為複雜,這家勞務公司經理對能否討到欠薪沒有把握,很是著急。後來有消息傳來:一些彝族工頭也往這廠里派送有工人。為討薪,這些彝族工人把這工廠包圍了起來,工廠來車運貨進不去,不知誰請了一些黑社會人員來向這些彝族工人尋釁開道,結果雙方廝打了起來,被公安帶到局裡接受做筆錄,但工廠並沒因此解圍。聽到這個消息,這家勞務公司的經理放心了,她告訴我:在這種事情上,彝族領工頭們從來就沒有輸過。果不其然,沒多久這家工廠所屬的村委會便墊付了欠薪,清退了該廠所有工人。
中央民族大學潘蛟教授和張曦教授在珠三角調查
對於當地公安而言,彝族農民工是群體性事件高發人群,因而是不安全的。那什麼又是安全的人群呢?好像是指那些被充分個體化,沒有任何族群意識和群聚力,遵紀守法的「公民」。然而,沒有這些彝族農民工的集體行動,按照合法程序,這工廠所欠的工人工資何時才能討回?還能不能夠討回呢?在上述那位勞務公司經理看來,恐怕是不能的。讓我不解的是,為什麼這些實際易受傷害的邊緣人群會被當做危險的,而這村委會,以及層層轉租工廠的老闆們卻被當做是安全的?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我以為,如果不是過分擔心廠主們的用工成本,切實落實國家有關勞工權益的保護條例,這或許才是從根本上避免上述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有效途徑,而且,由此騰省出來的維穩經費未必一定就比這些工廠實際上繳利潤稅收少很多。我了解過朝鮮族在韓國打工的情況,那裡的勞動法落實得十分到位,沒有人會擔心欠薪和工傷索賠,從而也沒有什麼「領工制」。
縱觀中國歷史,其實是不乏民族遷移的。西晉的永嘉之難,唐代的安史之亂,北宋的靖康之難所引發的衣冠南渡都是由於北方民族南移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人口遷移的趨勢幾乎一直都是由北往南,或由西往東。用歐文·拉鐵摩爾的話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影響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都是發生在它的內陸邊疆,用今日新清史史家的話講,也就是在中國歷史上,內亞因素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拉鐵摩爾看來,是「海洋時代」的到來才扭轉了這種人口遷移取向。隨著近代槍械,交通、礦業、通訊、金融的發展,中國的人口才開始向北,向西流動,這也就是說,走西口,闖關東其實不過是近代才有的事情。還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北方少數民族基本上是作為征服者進入漢族地區的,作為征服者他們卻被被征服者所同化,最終被融化消失在了漢族中。當然,南方的情況與北方是不同的。南方的歷史幾乎一直都是一個漢族人口流向少數民族地區,漢族文化不斷擴張的歷史。但是,今天的情況則不同了,儘管漢族人口進入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進程並未終結,但也形成了大批西南少數民族湧入東南沿海地區打工討生計的新趨勢。經濟學家或許可以稱這個趨勢表明了「劉易斯拐點」確實在逼近,大批少數民族進入東南沿海務工說明了中國製造已在動用它最後的勞動力儲備。但人類學家關注的則是全球化和人口流動所導致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文化和族群多樣性的增長。
當然,大批彝族、苗族能來東南沿海務工,反映了我國民族關係的根本改善,以及少數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在經濟上的高度整合。眾所周知,在1949年以前,這些少數民族是躲避漢族,不願意與漢族相處的。直到1956年以前,涼山彝族都還在搶掠或購買漢人到彝區做奴隸。那時一些彝族人甚至連被邀請來政府做官都不願意,遑論出來務工。
然而,今天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少數民族常駐人口的迅速增長對於我們理解我國民族關係的變化究竟意味著什麼?在過去,中國的民族關係基本上是區域與區域之間的關係,因此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常常可以被換喻成西部與東部的關係。這些少數民族真會像現有制度安排所預期的那樣,在東南沿海掙了錢寄回西部家鄉,促進西部經濟發展?據我所知,朝鮮族的情況似乎並不是這樣。他們一些人去了青島等地打工置業,一些人去了韓國打工。然而從韓國打工的錢卻沒有流回當東北延邊等地,而是流往青島煙台等地投資置業,以致東北朝鮮族地區人口空巢化突出,不得不採取撤校並鄉等舉措。
中央民族大學潘蛟教授和張曦教授在珠三角調查
如果這些少數民族回不去,或不願意回去,情況又會怎樣?他們會不會像歷史上那些進入漢族地區的北方少數民族一樣被同化和消解在漢族人群中?這在今天好像已不太可能。原因當然與我國現行的民族承認政策有一定關係,因為我國現今的民族政策反對搞民族強制同化,而且也不讓個人任意挑選自己的族屬。但在我看來,如果這是唯一的原因,那倒也好辦,因為民族政策總是可以調整的,更何況當上至中央的部長、北大清華的著名教授,下至普羅大眾都在呼籲國家調整現行民族政策,取消民族承認政治,推進公民政治,促進「民族融合」。但問題在於,歷史上的那些少數民族是作為征服者進入漢區的,作為統治者,他們擁有較多的身份選擇自由。今天的這些少數民族則不同,他們是作為農民工進入的,而現今的戶籍、社會福利等制度安排對於外來農民工實際上具有一定排斥性的,戶籍居民權實際上比「普遍公民權」更有意義。就東旭此書反映的情況看,涼山彝族農民工實際上位於東莞勞動力市場底端,是勞動力的後備軍,邊緣人群中的邊緣。在我看來,即便政策允許,即便彝族農民工願意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積極申請成為珠三角的合法公民,珠三角人民未必能答應。最近幾年發生的北京市高考生家長反對民大附中學生與他們分享在北京參加高考的權利等事件實際反映了所謂「普遍公民權利」實踐的空洞性。總之,社會上層想與下層找齊比較容易,但社會下層想與社會上層找齊卻不是那麼容易。由是觀之,長此以往,我國原有的區域化的民族關係是否會蛻變成一個一個區域內的社會分層關係,這是我的關注。無視現實中存在的實際差異,貿然推進民族融合,這聽上去當然美好,但實際上或許會陷國家於更為艱難的境地。
東旭的這本書較為詳細地揭示了珠三角涼山彝族農民工的工作、生活和組織狀況,探討了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勞動力市場分割與涼山彝族農民工呈現出來的性狀之間的複雜關係,無論對於理解中國經濟奇蹟還是對於理解中國民族關係的變化都具有積極意義。這本書的前身,東旭的博士論文曾獲得匿名評審專家和會議評審專家的一致好評,並獲得2014年度「余天休社會學優秀博士論文獎」。作為老師,我為他獲得的成就由衷感到高興,並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閱讀這本書,關注中國少數民族農民工以及正在變化著的中國民族關係。

人類學微刊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