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在生命里的信仰 ——韋斯琴書法藝術側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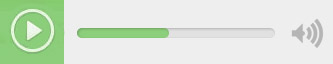
無事亂翻書。在林東威的《夜讀李商隱》中,讀到這樣的詰問:「你耗盡一生為萬物尋找對仗,可你自己的下聯是誰?」言下之意,難免有人生如夢的寂寞感和失重感;往幽深處探尋,背負生計的艱辛和苦澀,依舊充滿激情,執著邁向藝術殿堂的身影直逼一代人的精神原象。
每個人的人間道,都要有種在生命里的信仰,否則,便成了客串別人大片里的路人甲。
書壇書家集體衝出書齋又要回歸書齋的今天,現實功利的管道越鋪越密,小紅唱曲我吹簫式的所謂塵俗風雅,再與物慾糾纏不已,持續千年的生命況味與筆墨情懷往往會付之流螢飄風。當此時也,傳統文化的雨聲山嵐,匯聚成潮,書法端的應一筆一畫,引商刻羽,曲盡人情,洗濯人生。
對望韋斯琴的書法,獲得的便是此種信仰的魅力。生於煙樹凝碧、曲水一彎的江南山水人家,斯琴最初志於國畫,她的工筆荷花,一分色彩,一分氣息,妙手點染間令人有「江南好,風景舊曾諳」的興嘆。後於南藝求學時,改習書法,從此二十餘年中穿行於碑山帖林。
「我的專業是書法,但書畫同源,它們之間是互補的、共進的,無論作書法還是畫國畫,我都很痴迷中國傳統的藝術語言,痴迷於這數千年的文化積澱所散發出的獨特魅力。」
回頭反芻,斯琴的楷書花開花落自春風,既飽含傳統尺牘素養,又具有現代意義的重新建構;斯琴的行草,「枯木裡面有龍吟」「卷舒開合任天真」。作為當代具有標杆意義的女性書家之一,她的筆墨充滿了靈性和不斷靠近「永和九年」的人文氣質。盤石引弓,庖丁使刀,儼然大將風度。
雨腳連綿,蛙鼓陣陣;江南風物,養心可人。晚風為誰而追?江水為誰而逝?社鼓漁舟,綴著生命起興的種種意象,陶融出片片心中古意,最是蒹葭之致。蕪湖水脈是連接斯琴與書法的數據線,溫婉的江南女子慣有把桑葉轉化成絲綢的「春蠶吐絲」的本領。學碑習帖,自然量晴校雨、劍芒猶存。斯琴在《抄書的感覺》一文中說:
起初是抄蘇東坡,抄米芾,然後抄王羲之。那《蘭亭序》至少被我抄了五十遍。不過這是自願的,於是抄得仔仔細細,連王羲之寫錯了用墨划去的部分都一絲不苟地抄下來。還嘗試著用灑金紙、仿古紙、熟絹等不同質地的材料去抄,不僅抄,還默寫。抄完《蘭亭序》再抄《聖教序》,接著抄《文賦》、抄《書譜》、抄王鐸、抄徐渭……從古抄到今,再從今抄到古,居然越抄越有滋味。
斯琴以「抄」為日課,深入地對臨、背臨,這是對經典的借鑒。雖為「笨功夫」,關鍵在於能否領悟「抄」之三昧,能否真正做到尊重傳統,從而激蕩出與流俗隔絕的自家天地。「書以古為貴,不懂得抄古還真的難以理解書法之玄奧。」
線條生髮視覺內涵,筆墨激活生命情感。調墨作小楷,振筆書大草。在《碟中碟》都可以靠著湯帥成為經典的年代,斯琴始終有自己的風格試驗田需要堅守:
寫著寫著,就沒有信心了。但別扔筆,麻木的頂點,也正是感覺復甦的邊緣。寫著寫著,也就理解了。寫著寫著,也就有內涵了。
所謂的通會與創新,難拋一縷「獨行獨坐,獨唱獨酬還獨卧」的執念。對書法獨到的品藻需要在這樣抄寫的路上去完成。
宣紙有邊界,人生無彼岸。筆墨書寫中,沒有多少塵世舊夢值得亂懷。斯琴傾情地表達著對筆墨細節的掌控,向躁動著文化訴求的靈魂予以交代。對她而言,書法不是「華山論劍」,沒有必要槍口一致,一味地對著「展覽體」、流行書風,大諂其媚,書法還應作為一種修身與修養,一首懷鄉者的歌,輾轉安撫日益浮躁的心靈。
時常想,什麼樣的背景文字可以襯托斯琴書法線條的身姿,充分打開筆墨在宣紙上架構出的局面:情義兩心知,卻不必捅破那層窗戶紙?舍她那水佩風裳般的散文其誰!落葉霞飄,風檐展讀,《讓我慢慢地靠近你》(北嶽文藝版)、《藍》(海風版)、《弦情歲月》(江蘇文藝版)里,柔情密布,妙意天香,充盈著中國文人獨有的風雨心緒。筆觸所至,萬象往還,如同爵士樂中的煙熏腔,每每聽時,眼前都會有歲月煙雲、故園風景掠過。
母親的生態園正是我心靈的後花園,那兒才是我永遠的家,是我的靈魂休憩的地方。當我躺在窗下,聽秋雨撫蕉的時候,當秋蟲在晨露旁吟唱的時候,當麻雀在枝頭歡跳的時候,當母親清掃庭院的時候,我被這兒每一寸的溫柔撼動著。
這是七八年不曾回故鄉同母親過中秋的斯琴在《母親的生態園》中流露出來的精緻與細膩,給做慣了天涯客子者,以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無盡感喟:故鄉,一如我們的少年時,騎著破舊的單車,漸行漸遠。天地不仁,拈花一擊,人生種種因緣,易成隔膜,只要心靈的故園不蕪,心境自然澄澈。
然而這裡關注的並非斯琴散文所能表達出的人生高度,而是在藝術史的牆壁下,文學與書法的關係。兩種向度的人文景觀,色異形離乃表象,雙劍合璧為本質,都是使人獲得存在感和存在美感的有效途徑,同樣可以寓哲學化於詩意。
「淡淡的一縷書香,靜靜的幾許茶色,和著我的均勻的呼吸,這便是我的小楷,我的『斯琴散文』,以及我的並不奢侈的快樂。」斯琴的眼中,她的散文即是小楷,小楷便是散文,二者不失江南新竹般的明麗清爽,在書寫中釋放著生命的內涵。
巴爾扎克說:「一個藝術家比國王還強,他無拘無束,可以隨心所欲支配一個幻想世界。」在這一「幻想世界」里,散文氣質颯然脫胎成另一種筆墨精神。
有時,我也作行草,二王一路的,依舊是以雅為益,常於灰調子的灑金紙或仿古紙上的行筆,不太張揚,也不想刻板,於是偶有幾行草書(《十七帖》風格的)夾於行楷之間,以活潑氣氛,但有時流於刻意而失於自然。
一個人的文學水準往往令其自省和警覺,從而帶動與提升其筆墨個性與品位,增強線條的磅礴感和厚重感。斯琴的書法,「乃性情之流淌也。書乃心畫,畫乃心聲,興緻所至,情亦相隨。然筆墨性情,亦好比性情中人,須以成熟為依託。筆墨必得依託於成熟的藝術語言,之後才可言個性,再之後才可談品位。」
書法要真正邁向境界的門檻,文學修養和線條技法之外,還需做精神的遠足,回應一個關於山水的召喚,踐諾一種關於扁舟的等待。邁出書齋,並非要裹進現實中的一地雞毛,而是與自然天地相往還。伍立楊說:「境界的深蔚,最能融洽遠遊遠去的願望。」蘇子瞻的《記承天寺夜遊》,衣袂猶帶山中新月之清涼,長夜澈澈下,若緇衣僧人般秉玄妙輕功而來的身形,象徵的是打破現實虛無與執著之後的曠達開悟之境。令千年來幾多書家奮筆直書,追捧之至。由此,則往往足以一夕長大,人生圍城可解。無疑,斯琴喜歡遠遊,喜歡帶著筆墨,用自己的腳步撩響生命的琴音和鐘聲。歲歲年年人不同,她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異國他鄉。江南遊子的情感釋放地,多是筆墨築基升華處。
亂雲泥途,寫意山丘,慣能滋養藝事風姿。斯琴在《黃山紀旅三章》中云:
這是一個十分晴朗的日子,道路兩邊蔥鬱的青山在陽光下更顯生機盎然,晴空里幾片輕淡的白雲彷彿行吟的詩人,正緩行在微風裡。車至涇縣後,景色便越發秀麗起來,聚散在青山腳下的青瓦白牆的村莊,皆隱映在竹林里。鳥兒在竹枝上呼晴,溪水在竹林邊潺潺,牛羊在田頭漫步,農人在田間勞作,一切都顯得悠然而閑適。尤其當我們的車沿著盤山公路行至高處時,回望山坳里村落,真是片片桃源仙境。那由視線倏地傳至心靈的靜謐很難用語言準確描述。
從自然風情中誕生的「心靈的靜謐」,「讓竹竿與音樂、讓草皮與書畫、讓沙粒與珍珠、讓風和電……讓許許多多遙不可及的事物通過藝術的橋樑連接。而生命的快樂常常建立在對這些藝術結的感悟上」。斯琴所捕捉到的這些藝術之結的香火,斷然離不開自然靈性的互攝貫通,她的筆墨所投合的恰是青鞋布襪的山林襟懷,以及古代日常書寫中對生命情趣的高度駕馭能力。斜依窗檯,雪茄夾在指間,頻頻刷屏,沉浸在粗糙網路爽文里,如何會獲得深遠的人生感?
「吃酒八分醉,倚松看水流。」是一種對喧囂現實的詩意抵禦,是一場有意避世的人文撤退,筆墨的倒影、文學的神韻、旅行者的視野,涵泳著獨特的藝術情懷和哲學氣質,一旦與山外山處的夕陽接軌,沉醉之下,時常不辨歸路。對於斯琴而言,汲古出新、達其性情的書法創作高峰期終會到來,對於這份種在生命里的信仰,靜待時光去檢驗。念及此,眼前瞬間跳躍出的是,如秋燈般的螢火蟲千盞萬盞地掠過晉唐的庭院,以飽含深情的街頭為起點,揮筆恣意踏出長安來的馬蹄聲響。
推薦閱讀:
※基督教傳教人說宗教和信仰不一樣是什麼意思?
※道教為什麼式微?
※傳教士哀嘆葛培理支持羅姆尼 指責其妥協信仰, 基督郵報
※向日葵。你是我不變的信仰。
※通過什麼途徑可以建立一個堅實的、清晰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