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送新書】毛:「這是一個有風格的作家!」,送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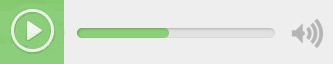
配曲:貝多芬《月光奏鳴曲》

寫在前面,當我寫下這個標題,誤會難免,引起非議,所以,需要澄清寫在前面。這句話的引用並無可非議之處,因為諸如高華在談論共產黨的勝利時也引用毛的話:「這純粹是軍事上的勝利。」,並且非常認可此判斷。「這是一個有風格的作家」 ,風格這東西,或許是一個 作家一輩子的追求,有些人可能一輩子也沒自己的風格,那他就無法被區分出來,當我們承認一個作家的風格,意味著他與眾不同了,不僅與大眾也與其他作家區分開來,或許,我們能這樣說,這位作家具有「特立獨行」的能力了。他是誰呢?
(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
他就是孫犁
今年是他去世的第十五個年頭
一位好朋友編輯
出版了孫犁的著作
《中國文化傳統是寬容的》一書
(好事說在前面轉發抽送一本)
《中國文化傳統是寬容的》
孫犁/著
我們直接上乾貨吧
這就是我們的風格
……
我們先發三篇文章供讀者鑒賞
(讀《史記》記(上)、(中)、(下))
讀《史記》記(上)
——節選自《中國文化傳統是寬容的》
文/孫犁
一
裴駰《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耕堂按: 索隱以刺客為遊俠,非也)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 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
耕堂曰: 以上,裴駰(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論司馬遷之言,並肯定之。讀《史記》前,不可不熟讀此段文字,並深味之也。班之所論,不只對司馬遷,得其大體,且於文章大旨,可為千古定論矣。短短二百字,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史記》所依據之古書;(二)《史記》敘事起訖;(三)《史記》詳於秦漢,而略於遠古;(四)班固所見《史記》缺處;(五)班固總結自劉、楊以來,對《史記》之評價,並發揮己見,即所謂實錄之言,為以後史學批評、文學批評,立下了不能改易的準則。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麼理,就會敘出什麼事;敘什麼事,就是為的說明什麼理。作家與文章,主觀與客觀,本是統一體,即無所謂主體、客體。過於強調主體,必使客體失色;同樣,過於強調客體,亦必使主體失色。
「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也是很難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觀察、理解、文辭)深厚的修養。因為既辯,就容易流於詭;質,就容易流於俗。辯,是一種感情衝動,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嘩眾,就必然流於俚了。
至於「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為這常常涉及許多現實問題: 作家的榮辱、貧富、顯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這樣的文章、著述,在歷史上就一定成為鳳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東西了。
奉勸有志於此的同道們,把班固這三十個字,寫成座右銘。
希望當代文士們,以這三十個字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寫的文字: 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實的,是沒有虛美的,是沒有隱惡的。
然而,這又都是獃話。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實,可為名人;虛美,可得好處;隱惡,可保平安。反之,則常常不堪設想。班固和司馬遷,本身的命運,就證實了這一點。
無論班固之評價司馬遷,或裴駰之論述班固,究竟都是後人議論前人,不一定完全切當,前人已無法反駁。班固指出的司馬遷的幾點「是非」,因為時代不同,經驗不同,就不一定正確。這就是裴駰所說的:「人心不同,傳聞異辭。」
二
班固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正義》曰:
大道者,皆稟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
耕堂曰: 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後檢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有《文帝黃老之治》一節,所言不過慈儉寬厚。又有《黃老之疑義》一節,讀後乃稍明白。茲引錄該節要點如下:
一、 漢時與儒術為敵者,莫如黃老。
二、 黃老之名,始見《史記》,曾出現多次。
三、 《史記》以前,未聞此名。
四、 實與黃帝無涉,與老子亦無大關係。
五、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學道論於黃生,黃學貴無而又信命,故曰黃老。
六、 漢時民間盛行壬禽占驗之術,謂之黃帝書,是民間日用之書。黃老學者,即以此等書而合之老子書,別為一種因循詭隨之言。
七、 漢高、文、景諸帝,皆好黃老術,不喜儒術。以竇太后(景帝之母)為甚,當她聽到儒生說黃老之學,不過是「家人言」(即僮隸之言)時,就大怒罵人:「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並命令該人下圈刺豬。那時的豬,是可以傷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沒有喪命。
延安整風時,曾傳說,知識分子無能力,綁豬豬會跑,殺豬豬會叫。
「文革」時各地幹校,多叫文弱書生養豬,鬧了不少笑話。看來,自古以來,儒生與豬,就結下了不良因緣。然從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說之可信。本是討論學術,當權者可否可決,何至如此惡作劇!
三
夏曾佑還指出: 司馬遷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歸本道家,此老學也。
在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馬談以為: 陰陽家多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馬遷遵循了以上見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觀,這是沒有疑義的。他這種黃老思想,當然已經有別於那種民間的占卜書,也有別於竇太后的那種僵化和固執,是思想家的黃老思想,作家的黃老思想。這種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寫作之中。
黃老思想,很長時期,貫穿在中國文學創作長河之中。這種思想,較之儒家思想,更為靈活開放一些,也與文學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為作家接受。
耕堂曰: 作家必有一種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時為繼承傳統,有時因生活際遇。際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於生活,形成創作。此即所謂「天人之際」。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異,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樣。然具備自身的思想,為創作的起碼條件,具備自身的生活經歷,則為另一個基本條件。兩相融合、激發,才能成為作品。
然文場之上,亦常出現,既無本身思想,亦無本身生活的人。從歷史上看,此等文人,約分數型: 有的,呼嘯跳躍,實際是嘍羅角色。或為大亨助威,或為明星搖旗。有的,以文場為賭場,以文字為賭注,不斷在政治寶案上押寶。有時紅,有時黑,有時輸,有時贏,總的說來,還算有利可圖,一般處境不錯。但有時,情急眼熱,按捺不住,赤膊上陣,把身子也賭上去,就有些冒險了。有的,江湖流氓習氣太盛,編故事,造謠言,賣假藥,戴著紙糊的桂冠,在街頭鬧市招搖。有的,身處仕途,利用職權之便,拉幾位明星作陪,寫些順水推舟,隨波逐流,不痛不癢的文章發表,一腳踏在文藝船上,一腳踏在政治船上,並準備著隨時左右跳躍的姿態。此種人,常常一舉兩得,事半功倍。然都是湊熱鬧,戲一散,觀眾也就散了。
四
歷代研究《史記》的學者,對班固的論點,也並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駰說:「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比較含蓄。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則對班氏進行尖銳反批評,並帶有人身攻擊的氣味。他認為:「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該通。」他認為這是司馬遷的著述精神。
「班固詆之,裴駰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剝《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優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馬優劣論」,多為後人好事者所稱引,其實是沒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點,並非詆毀;多少年寫多少字,是因為今古不同,時間有遠近,材料有多少造成。並非文章繁簡所致。稱引先人與否,不能決定作品的優劣。張守節因治《史記》,即大力攻擊《漢書》,殆不如裴駰之客觀公正矣。
《正義》並時有矛盾。在後面談到班固指出的這三條缺點時,他又說:「此三者,是司馬遷不達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黃老,上面已經談過。序遊俠,羞賤貧,前人多以為,司馬遷所以著意於此,多用感情,是與其身世有關。如遭到不幸,無人相助,家貧不能自贖等等。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為,並非完全是這麼回事。司馬遷以續《春秋》自任,六藝之中,特重史學。史學之要,存實而已,發微而已。時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當先有所見,並看出問題。他對遊俠、貨殖,都看做是社會問題,時代癥結。遊俠在當時已形成能影響政治的一種勢力,從緩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顯看出。在貨殖方面,司馬遷詳細記錄了當時農、工、商各界的生產流通情況,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政治的影響。都是做了深入調查,經過細心研究,才寫出的。兩篇列傳,都是極其寶貴的歷史文獻。
耕堂曰: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記》三點錯誤,實不足為《史記》病,反彰然表明,實為《史記》之一大特色,一大創造。
各行各業,均有競爭,競爭必有忌妒。學者為了顯露自己,不能不評譏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猶不失為學術。如出自不正之心,則與江湖藝人無異矣。
近人為學者,詆毀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風甚熾。並非近人更為沉落不堪,實因外界有多種因素,以誘導之,使之急於求成,急於出名,急於超越。如文化界之分為種種等級,即其一端。特別是作家,也分為一、二、三等,實古今中外所從未聞也。有等級,即有物質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長勢利之欲。其競爭手段,亦多為前所未有。結宗派,拉兄弟。推首領,張旗幟。花公家錢,辦刊物,出叢書,培養私人勢力,以及亂評獎等等。
以上,均於學術無益,甚至與學術無關。亦不能出真正人才。但往往能得到現實好處,為淺見者所熱衷。(原載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滿庭芳」)
讀《史記》記(中)
一
《太史公自序》: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耕堂按: 包括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以上是司馬遷自敘幼年生活、讀書,以及兩次旅行所至地方。這些,都是《史記》一書創作前的準備,即學識與見聞的準備。自司馬遷創讀書與旅行相結合,地理與歷史相印證,所到一處,考察民風,收集口碑遺簡,這一治學之道,學者一直奉為準則,直至清初顧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後面接著敘述,他如何受父命、下決心,完成這一歷史著作: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耕堂按: 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綴集之)石室金匱之書。
這還是材料準備階段,共用五年時間。《史記》正式寫作,於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後,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寫作受到很大打擊。在反覆思考以後,終於繼續寫下去,完成了這部空前絕後的著作。
當時的漢朝,並不重視學術文化,他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也沒有人過問。《史記》的第一個讀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東方朔。東方朔確是一個飽學之士,文辭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優畜之,正在過著「隱於朝廷」、「隱於金馬門」的無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馬遷引他為知己,把著作先拿給他看。東方朔的信條是:「崛然獨立,塊然獨處;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司馬遷的信條是:「不趨勢利,不流世俗。」兩個人所以能說到一處。東方朔在司馬遷的書上,署上「太史公」三個字。後人遂以《史記》為太史公書。
班固說: 遷既死,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序》,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它的流傳,以及研究注釋,遠遠不及班固的《漢書》熱鬧。很長時間,是不為人知,處境寂寞的。
二
關於司馬遷及其《史記》,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據他的自序。班固所為列傳,只多《報任安書》一文,其餘亦皆襲自序。
耕堂曰: 後之論者,以為《史記》一書,乃司馬遷發憤之作。然發憤二字,只能用於李陵之禍以後;以前,欽念先人之提命,承繼先人之遺業,志立不移,只能說是一種堅持,一種毅力,一種精神。這種精神,遇到意外的打擊、挫折,不動搖,不改變,反而加強,這才叫做發憤。發憤著書,這種人生意境,很難說得清楚,惟有近代「苦悶的象徵」一詞,可略得其彷彿。
凡是一種偉大事業,都必有立志與發憤階段。立志以後,還要有準備。司馬遷的準備,前面已經說過了。
人們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但才能二字,並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個人努力,和適當的環境。努力和環境,可以發展才能,加強才能。
所謂才能,常常是在一個人完成了一種不平凡的工作之後,別人加給他的評語,而不是在什麼也沒有做出之時,自己給自己作的預言。自認有才,或自稱有才,稍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經過長期努力,在一種事業上,做出一定成績的時候,才能如此說。
在歷史上,才和不幸,和禍,常常聯在一起。在文學上,尤其如此。所謂不幸、禍,並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災;常常是指人禍。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親友,均無能為力,不能挽救的一種突然事變,突然遭際。司馬遷所遭的李陵之禍,他在《報任安書》中,敘述、描繪的,事前事後的情狀,心理,抉擇,痛苦,可以說是一個有才之士,在此當頭,所能做的,最為典型、最為生動的說明了。
這種不幸,或禍,常常與政治有密切聯繫,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後果。姑不論司馬遷在書信前面,列舉的西伯以下八個王侯將相,他們之遭禍,完全是政治原因,他們本身就是政治。即後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個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禍,也無不直接與政治有關。
司馬遷把遭禍與為文,聯結成一個從人生到創作的過程,稱之為: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這是一個極端不幸、極端痛苦的過程,是一個極端令人傷感的結論。更不幸的是,這個結論為歷史所接受,所承認,所延演,一無止境。
三
《秦始皇本紀》: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 博士齊人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耕堂曰: 以上為秦始皇時,李斯著名之建言,焚書坑儒之原始文件。余詳錄之,以便誦習,加深對這一歷史事件的準確印象。李斯說這段話之前,是一位武官稱頌始皇的功德,始皇高興;接著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發表意見。
這一事件的要害處,為「以古非今」。這事件的發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業大著,志滿驕盈之時。他現在所想的,一是鞏固他的統治,一是求長生。鞏固統治,李斯的主張,往往見效。長生之術,則只有方士,才能幫忙。
看來,此次打擊的對象是儒,重點是《詩》、《書》(《詩》、《書》,也不是全燒掉,博士所職,還可以保存)。但這時的儒生和方士並分不清楚,實際是攪在一起。始皇發怒,以致坑儒,是因為給他求仙藥的人(侯生和盧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餘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難說了。
儒家的言必稱堯舜,在孔子本身就處處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參政思想很濃,非要試試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別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衝突較量,一次徹底的大失敗。既然並立朝廷,兩方發言,機會均等,即為政治鬥爭。後人引申為知識與政治的矛盾,或學術與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誇大了。但這次事件是一個開端,以後的黨錮、文字獄、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著這條路走下來的。這也算是古有明訓吧!
四
政治需要知識和學術,但要求為它服務。歷史上從未有過不受政治影響的學術。政治要求行得通見效快的學術。即切合當前利益的學術。也可以說它需要的是有辦法的術士,而不是只能空談的儒生。所以法家、縱橫家,容易受到重任。
儒家雖熱衷政治,然其言論,多不合時宜,步入這一領域,實在經歷了艱難的途徑。最初與方士糅雜,後通過外戚,甚至宦豎,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揚仍舊,其進取方式,則不斷因時勢而變易。既如此,就是隨時吸收其他各家的長處,孔孟之道,究竟還留有多少,也就很難說了。所以司馬遷論述儒家時,也只承認它的定尊卑,分等級了。
在儒學史上,真正的岩穴之士,是很少見的。有了一些知識,便求它的用途,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進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險,聰明一些的人,就選擇了其他的途徑。《史記》寫到的有兩種人: 一是像東方朔那樣,身處廟堂,心為處士,雖有學識,絕不冒進,領到一份俸祿,過著平安的日子,別人的挖苦嘲笑,都當耳旁風。另一種則是像叔孫通這樣的人。
《叔孫通列傳》:
於是叔孫通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當叔孫通替劉邦定好朝儀以後: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司馬遷雖然用了極其諷刺的筆法,寫了這位儒士諸多不堪的言詞和形象,但他對叔孫通總的評價,還是:
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這是司馬遷,作為偉大歷史家的通情達理之言。因為他明白: 一個書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樹,得到社會的承認,在現實條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著重點出的,是「與時變化」這四個字。這當然也是他極度感傷的言語。
漢武帝時,聽信董仲舒的話,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並不是儒家學說的勝利,是因為這些儒生,逐漸適應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當世之要務」。(一九九〇年三月六日)
讀《史記》記(下)
一
司馬遷在寫作一篇本紀,或一篇列傳時,常常在文後,敘述一下自己對這個地方,或這個人物的親身見聞,即自己的考察、感受、體驗心得,以便和寫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證,互相發揮,增加正文的感染力量,增加讀者的人文、文史方面的知識、興趣。茲抄錄一些如下:
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雲。(《孔子世家》)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孟嘗君列傳》)
太史公曰: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蒙恬列傳》)
有時是記一些異聞,如:
太史公曰: 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公、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刺客列傳》)
他否定了一些關於燕太子丹和荊軻的傳說。而他得到的材料,則是出自曾與夏無且交遊過的人。夏無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荊軻刺秦王,殿廷大亂的時候,用藥囊投擲荊軻的那位侍醫。這樣,他的材料,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有時是見景生情,發一些感慨:
太史公曰: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 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樊酈滕灌列傳》)
二
對歷史事件,司馬遷有自己的見解;對歷史人物,司馬遷常常流露他對這一人物的感情。這種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結尾處,使讀者迴腸盪氣。這是歷史家的評判。但又絕不是以主觀好惡,代替客觀真實。最明顯的例子,是對於劉、項。
在《項羽本紀》之末,司馬遷流露了對項羽的極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項羽推崇為舜的後裔。對他的失敗,表現了極大的惋惜。但項羽的失敗,是歷史事實。司馬遷又多次寫到: 項羽雖然尊重讀書人,但吝惜官爵;劉邦雖多次污辱讀書人,對封賞很大方,「無恥者亦多歸之」,終於勝利。歷史著作,除佔有材料,實地考察無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馬遷所到之處,都進行探尋訪問,這種精神,使他的《史記》不同凡響。後人修史,就只是坐在屋裡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會再有《史記》這樣的文字。
司馬遷雖有黃老思想,但在一些倫理、道德問題的判斷上,還是儒家的傳統。他很尊重孔子,寫了《孔子世家》,又寫了弟子們的傳記。記下了不少孔子的逸事和名言。他也記下了老子、莊子。對韓非子的學說,他心有餘痛,詳細介紹了《說難》一篇。其中所謂:「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今日讀之,仍覺十分警策。在學術上,他是兼收並蓄的,沒有成見的。析六家之長短,綜六藝之精華,《史記》的思想內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 余嘗怪,古時文人,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敗者?蓋彼時文人自己,亦處失意不幸之時。如已得意,則必早已腰滿腸肥,終日忙於赴宴及向豪門權貴獻殷勤去矣!又何暇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頌德,應景應時之作了。
三
耕堂曰: 《史記》出,而後人稱司馬遷有史才。然史才,甚難言矣。班固「實錄」之論,當然正確,亦是書成後,就書立論,並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礎,作全面敘述。
文才不難得,代代有之。史纔則甚難得。自班、馬以後,所謂正史,已有廿余種,部頭越來越大,而其史學價值,則越來越低。這些著述多據朝廷實錄,實錄非可全信,所需者為筆削之才。自異代修史,成為通例以來,諸史之領銜者,官高爵顯;修撰者,濟濟多士,然能稱為史才者,則甚寥寥。因多層編製,多人負責,實已無人負責。褒貶一出於皇命,哪裡還談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為史才之基礎為史德,即史學之良心。良心一詞甚抽象,然正如藝術家的良心一詞之於藝術,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種認真負責的精神。
司馬談在臨死時,告訴兒子: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這就是父子兩代,史學良心的發現和表露。
用現在的名詞說,就是史學的職業道德。這種道德,近年來不知有所淡化否,如有,我們應該把它呼喚回來。
史學道德的第一條,就是求實。第二就是忘我。
寫歷史,是為了後人,也是為了前人,前人和後人,需要的都是真實兩個字。前人,不只好人願意留下真實的記載和形象;壞人,也希望留下真實的記載和形象。誇大或縮小,都是對歷史人物的污衊,都是作者本身的恥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現,非同文才的表現。它第一要求內容的真實;第二要求文字的簡練。
史學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傳世,高低之分全在這兩點。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後序》中,稱讚司馬遷:「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實;「詞省」、「文微」,就是簡練。
添油加醋,添枝加葉,把一分材料,寫成十分,亂加描寫,延長敘述,投其所好,取悅當世,把乾菜泡成水菜等等辦法,只能減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著述聲譽。
至於有意歪曲,著眼勢利,那就更是史筆的下流了。
今有所謂紀實文學一說。紀實則為歷史;文學即為創作。過去有演義小說,然所據為歷史著作,非現實材料。現在把歷史與創作混在一起,責其不實,則詭稱文學;責其不文,則託言紀實。實顧此失彼,自相矛盾,兩不可能也。
所謂忘我,就是忘記名利,忘記利害,忘記好惡,忘記私情。客觀表現歷史,對人對己,都採取「死後是非乃定」的態度。
當代人寫當代事,牽扯太多,實在困難。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難以寫好。沈約《宋書·自序》說:
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事屬當時,多非實錄。
班固能撰《漢書》,是史學大家。據說他寫的「當代史料」,幾不可讀。這就是劉知幾說的「拘於時」的著作,不易寫好。
能撰寫好前代史傳,而撰寫不好當代的事,這叫「拘於時」。而司馬遷從黃帝寫到漢武帝,從古到今,片言隻字,人皆以為信史。班固的《漢書》,有半部是抄錄《史記》。就不用說,後代史學界對他的仰慕了。這源於他萌發了史學的良心。
四
我有暇讀了一些當代人所寫的史料。其寫作動機,為存史實者少,為個人名利者多。道聽途說,互相抄襲,以訛傳訛,並擴張之。強寫偉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長文章,多換稿費。有的胡編亂造,實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沒有精力,也沒有機會,去閱讀那些大小報刊,無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辯駁。如此,這些人就更無忌憚。這還事小,如果以後,真的有人,不明真偽,采作史料,貽害後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這是我的杞憂。其實,各行各業,都有見要人就巴結,見名人就吹捧的角色。各行各業,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時是幫忙,多數是幫閑,有時是吹喇叭,有時是敲邊鼓。你得意時,他給你臉上搽粉;你失意時,他給你臉上抹黑。
但歷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將掃除一切污穢,淘盡一切泥沙。剝去一切偽裝,削去一切蕪詞。黑者自黑,白者自白。偉者自偉,卑者自卑。各行各業,都有玩鬧者,也不乏嚴肅工作的人。歷史,將依靠他們的篩選、澄清,顯露出各個事件,各個人物本來的面目。一九九〇年三月九日寫訖讀《史記》記(跋)讀《史記》記(跋)清人有關《史記》之著述甚多,多為讀書筆記。最有名者,為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之《讀書雜誌》。我有金陵書局刻本。此書,我在中學讀書時,謝老師即為介紹,極為推崇。然中學生《史記》原書,尚未讀懂,更未全讀。此師以己之所好,推及於學生,實無的放矢也。今日讀之,興趣亦寡。序言,略有情致,其他皆個別文字之考證,甚枯燥無味。我尚購有王鳴盛、錢大昕、趙翼之著作,皆為中華書局近年排印本。其治學方法與王氏同,亦皆未細讀,近人整理的郭嵩燾之《史記札記》,考據之外,還有些新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治學方法,治學愛好,終生孜孜,流連忘返。這種意趣,後人是難以想像的。此後,魯迅先生於《史記》研究,頗有新的見解,惜《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論及司馬遷者,文字不多。
其實,《史記》有集解、索隱、正義,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時之考證,對於讀這部書,文義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認,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亂,於讀原書,並無多大好處。所以,我讀古書,總是採取硬讀、反覆讀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兩種《史記》: 一為涵芬樓民國五年影印武英殿本,一為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此本也是據武英殿本排印的,余慮其有誤植,故參照影印本。這兩種本子,拿放都很輕便,字大清楚,便於老人閱讀。
我沒有購買中華書局近年標點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沒有斷句,更沒有標點。此次引文,標點都是我試加的,容有錯誤。發表前,請張金池同志,逐條參照中華標點本,以求改正。這是很麻煩的事,應當感謝。
我以為: 讀書應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經歷及用心。然後,就其文字內容,考察其實學,以及由此而產生之作家風格。我這種主張,不只自用於文學作品,亦自用於史學著作。至於個別字句之考釋,乃讀書之末節。
黃卷青燈,心參默誦,是我的讀書習慣。此次讀《史記》,仍舊用這種辦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讀到哪裡,今夜已不省記。讀時有些心得,稍縱即又忘記。欲再尋覓,必需檢書重讀,事倍而功半。
但還是讀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讀一卷,或僅讀數頁。本紀、世家、列傳,及卷首卷尾部分,總算粗讀一過。其他,實仍未讀也。回憶自初中時,買一部《史記菁華錄》,初識此書。時至今日,用功僅僅如此,時間之長,與收穫之少,可使人慚愧。讀書,讀書,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讀多少好書,只能自己心中有數了。
至於行文之時,每每涉及當前實況,則為鄙人故習,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變者也。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晨記
註:本文摘自
《中國文化傳統是寬容的》
推薦閱讀:
※新書簡介——明朝白銀、海洋貿易與制度內卷
※【薦讀】20本值得一讀的新書,我們讀書吧!
※南部新書(宋)錢易黃壽成 校點簡介
※集類《敦煌變文集新書》卷四
※樓宇烈:關於《荀子新注》 | 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