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宗教的儒學,如何承負信仰?(下)
教化的儒學,儒學的教化
點擊上方「藍字」可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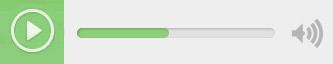
義理的體系與信仰的系統
——考察儒家宗教性問題的一個必要視點
文 | 李景林
小編引言
儒學與宗教的關係是理解儒學精神的一個大問題。學界的一般看法是:儒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更應被視為是一套哲學體系;同時認為儒學具有宗教性,可以提供信仰的功用。這不免讓人有所疑竇:是哲學為何又是信仰?不是宗教為何又說具有宗教性?……其實關於儒學與宗教的問題,學界爭論已久,其間義理糾纏煩繞,以至難有透說。儒學到底是宗教還是哲學?如果不是宗教,那麼儒學的產生與作為其思想土壤的古初宗教信仰系統之間之關係應如何定位?如果儒學是哲學,儒學又為何長久以來一直發揮著宗教信仰般的教化功效?三.義理的體系與教化的方式
康德把所有的宗教區分為「追求恩寵的宗教」與「道德的宗教」兩類。前者希望僅僅通過祈求上帝的協助而得到永遠的幸福或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後者則秉持這樣的原則:每個人僅須盡己力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而不必和無意祈求上帝之協助。康德認為,只有這種「道德的宗教」才配稱為「真正的宗教」。[1]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周代的禮樂文化,雖由天帝之倫理規定而進至「倫理宗教」的範圍,但其作為康德意義上的「道德的宗教」,卻尚未真正得到確立。而其實現其作為「道德的宗教」或「真正的宗教」這一本質性的跨越,則正有賴於儒家哲學的創造與轉化。
鄭開教授從結構的意義上把周代的禮樂文化界定為一種「德禮體系」。「德」的一面,表示建構於禮的精神氣質,「禮」的一面,則呈現為制度和秩序。[2]不過,若從形上學的角度看,周人的「德」,尚未形成為一個以自因或自律為根據的自足性概念,因而無法構成社會倫理體系的價值基礎。學者已注意到,西周「德」這一觀念的內涵,主要側重於與政治行為相關的「行」。[3]而這「德」的本原,並非發自於內,或人自身的決斷,而是出於一種對政治後果的考量和功利性的動機。故周世的宗教系統,基本上體現了一種功利主義的宗教觀念。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天為至善的本原。《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云:「《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是言天帝為「德」或至善之本原。另一方面,人之行德,則又以功利為目的。天之佑有德而懲無德,主要表現為天命亦即王權的轉移。在周人看來,夏殷先王因能「明德恤祀」而受命於天,而又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4]周人以小邦承大命,其言天命,語多驚懼,表現出一種很深的憂患意識。而其所謂「敬德」,亦非出於對人自身道德使命之自覺與決斷,而是出於王權永續之功利動機。《尚書·召誥》:「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公告誡成王要以夏殷的失德墜命為鑒戒,特彆強調要「疾敬德」,而此「敬德」,行德之目的,則要在「祈天永命」。可見,周人之宗教觀念,乃以天為至善之本原,認天帝為一「道德的神」;但人之敬德、行德,目的卻在功利,人乃被理解為一功利性的存在。這種對人的功利性理解,與其神性內在於人的命義是自相矛盾的。
商周文明之連續性與整體性的特徵,使其宗教的觀念,具有一種神性內在於人的本質義涵。神性內在,表現於人,人性亦當具神性而有「善」的內在規定。不過,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到,這種神性內在,在周代的宗教和信仰系統中主要體現為一種「民彝物則」本原於天的觀念,尚未能在「德」的層面上達到自覺。周代「性」的觀念,基本上被理解為一種基於自然生命的慾望要求,其所謂「節性」,亦只是由「敬」或敬德而來的對慾望的節制[5]。因此,當周末社會高下陵夷,社會劇烈變動,德、福顯著地不能達到一致的現實境域下,天之作為至善本原的神聖超越性及其德福一致之確證者的意義,必會遭到懷疑與否定。在《詩經》反映厲、幽時代的詩中,出現有大量疑天的詩句,就表明了這一點。[6]由此,禮作為倫理的原則,亦趨於形式化,甚至成為諸侯爭霸,權臣竊國之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周代缺乏自身自律性德性基礎的「德禮體系」,必然會趨於崩解。西方「破裂性」的文明,在宗教上斷神人為兩界,以人負原罪而不具神性,故需上帝之神恩拯救,人由是而有對上帝之景仰敬畏之心與恪守上帝立法之義務。而在商周這樣一種「連續性」的文明形態中,人並無如基督教那樣的原罪意識。因此,如不能將其宗教和信仰系統所本具的神性內在義轉變為一種內在的德性或人性的自覺,周世禮樂文明的「德禮」結構,便無法獲得理論上的自洽性和存在上的必然性;其宗教和信仰系統之作為「倫理宗教」、「道德宗教」之義,亦無由真正得以確立和圓成。
人是一種矛盾性的存在者。一方面,人是一種「定在」,因而其存在有自身的限度。基督教斷神人為兩界,以人不具神性,是凸顯了人的存在之限定性、有限性的一面。中國連續性的文明所構成的神道系統,則凸顯了人的存在的另一面,即神內在於人,神人之內在連續和本原統一性的一面。這後一方面,經過東周社會因王綱解紐,禮壞樂崩,神聖價值失墜所引發的理性反思,在儒學的系統中獲得了一種人的存在層面上的自覺及由此而來的人性觀念上的轉變。一方面,這一自覺和轉變,構成了一種哲理和思想的系統,具有西方學者所謂的「哲學的突破」的意義;同時,經由此「哲學的突破」的奠基,傳統的信仰系統亦達到了自身真理性的自覺,實現了其作為「道德的宗教」之本質性的轉變。
儒學所達成的這一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孔子通過對「義、命」的內在區分,發現人之唯一可自作主宰、自由決斷的最本己的可能性,乃在於行「仁」由「義」,從而轉變周人對人的功利性理解,把「善」的原則轉變為人之本有的規定。
孔子所關注的角度,仍然是商周信仰體系中那個「神道」的方面。如前所述,這神道的內容,事質上是一個倫理的、規則的體系。在周人的觀念中,這一套民彝物則,悉源出於天或天命。孔子繼承了這一觀念,但對這個統攝人倫物則的天命觀念,作出了一種「義」與「命」的內在區分。《孟子·萬章上》:「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這個概括,深得孔子學說之神髓。周人所謂「天命」,本包涵「德、福」兩方面內容。天命有德而討有罪,人之德福之一致性,乃由天或天命來保證。「天」為人至善之本原;人「祈天永命」,其動機、目的卻在於求福報。孔子則通過對人的存在所本乎天的天命之內涵所作內在的義、命區分,實現了一種人的存在自覺上的意義翻轉:仁義在我而福命在天。
孔子亦以天為至善的法則和本原,此與周人同。[7]不過,在孔子看來,天命於人,乃包涵有相互關聯的兩方面內容:人行之界限與事功之結果。前者屬「義」,後者則屬「福」。對此,《論語》有相當多的論述。《雍也》:「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顏淵》:「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憲問》:「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微子》:「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凡此所謂「天」「命」,皆指人行之福報和行為之效果而言。對此一方面,人無決定之權,故屬諸天或者命。而另一方面,人之行仁、由義,其決定之權,卻在內而不在外,在我而不在人。《論語·顏淵》:「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述而》:「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里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些論述,表現了孔子對「人」的一種全新的理解。在孔子看來,行仁、義乃是人唯一不靠外力,而憑自己的意志決斷和力量所可求可欲,並實現於自身的東西,因而它規定了人的本質,為人的本性之所在。人之行為的價值,在於其選擇躬行其所當行(仁、義);人行之結果如何,則不在人所直接可求之範圍,故只能歸諸「命」或「天命」。而這「義」與「命」之間,又有一種動態的、內在的統一性。人的道德或行為抉擇,既表現了人對自身使命之了解和自覺,亦具有賦予其行為及其結果以正面與負麵價值之意義。人行其所當行,得其所應得,其結果,既是天命之實現,同時亦是其人格和存在之完成,此即孔子所說的「知命」或「知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把是否能夠「知命」或敬畏「天命」,看做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根本判准[8]。「知命」與「知人」,對於人的存在與價值之實現,在孔子看來,實一體兩面,不可或分。這種對義、命關係的理解,使商周的天命觀念產生了一種價值上的內轉:把行德行義由外在性的祈天邀福之手段,確立為為人之最本己的能力和人性之內涵。孔子說「仁者人也」[9],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在這個意義上,善的原則乃轉變為人之本有的規定。孔子對「人」的這一重大發現,確立了儒家人性本善的思想基調和價值取向,規定了以後儒家天人關係觀念的基本內涵。
孔子所奠定的儒學這一精神方向,經孔子後學至孟子的發展,形成了自身完備的學說體系。子思《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道」即人道(其內容為禮或禮樂),「教」者教化。是言人倫教化,悉本諸天命之性。近年出土簡帛《五行》篇,以人心本「悅仁義」、「好仁義」,而言「心貴」;並以此為仁義之「端」,謂人能「進端」、「充端」,即擴充實現此仁義之「端」,便可最終實現仁德,成就為君子[10]。郭店簡特別重視樂教。《性自命出》「凡道,心術為主」之說,與《禮記·樂記》相通,所重在人的情態生活,突出強調樂教的教化之效,並以「反善復始」的「復性」義規定此教化成德之本質內涵[11]。仁義既為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為人心所悅所好,則其必為人性之所本具之先天內容。
由此,孟子進一步轉孔子之「義命」之論為「性命」之說,直以仁義規定人性之內涵。《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人之慾望要求及功利性滿足,與仁義禮智聖的道德規定,皆本原於天或天命。孟子乃於此進一步作「性、命」之區分:以前者為「命」,後者為「性」。其思想理路全本之孔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告子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盡心上》:「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孔子講「欲仁仁至」、「求仁得仁」,孟子亦以求之之道的區別來區分「性」「命」。仁義禮智是「求則得之」、「求有益於得」、「求在我者」,其所主在我,本乎人心,是人唯一可以通過反躬自省,自我決斷、自作主宰而能夠達到和實現的東西,故可謂之「性」。與此相對,人心之慾望要求和功利性的滿足,則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其受制於各種外部複雜的因素,其決定之權在「他」而不在「我」,只能由乎其道而俟其所成,故謂之「命」。仁義禮智諸德為人心所直接「可欲」、「可求」者。孔子既說「欲仁仁至」,又說「求仁得仁」,可知「可欲」與「可求」,可以互訓。不過,二者又各有側重。孟子言仁義禮智之「可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偏重在「思」或內省反思;言「可欲」,則著重於仁義、理義之「悅我心」[12]的意義,偏重在情意呈顯一面。是仁義禮智不僅為人心內省反思可得,同時亦在人性中具有先天的內容,儒家性本善之義由是而得以證立。
孔孟仁義在我而福命在天之義,並不意謂福命全然無關乎人。孟子既區分「正命」與「非正命」[13],又有「修身」以「立命」之說[14],意在指出,「義」與「命」,人的價值抉擇與其事功效果之間,有著一種內在的、存在實現意義上的因果關聯性。仁義內在於人之實存,為人行之所當然之則;人之處身境遇,則有順逆窮通之異。在儒家看來,「命」或「福」固非人力所直接可與,但亦非現成擺在某處的一種宿命。「命」之所以存在正面(正命)和負面(非正命)價值之差異,乃是因為,人的價值抉擇在轉變其當身處境的同時,亦對其所行之結果發生著一種內在的賦義的作用。小人固「無義無命」[15],而君子之「正命」,則必由其人道之抉擇所「立」並賦予它以正面的價值。因此,「天命」並非某種外在於人的現成設定與宿命,而是一種存在的「實現」。這個實現,乃由乎「自力」,由乎人性的自覺與完成。商周連續性文明,所包涵之神性內在、神人內在連續的精神,由此義命分合之動態實現的義理系統,始達到本質性的自覺,社會信仰系統之道德自律基礎,亦由此而得以奠立。
第二,與此相應,孔子提出了一種新的神靈觀念和對待天命鬼神的態度。或謂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主張「敬鬼神而遠之」,是否定鬼神。其實,孔子此一態度,恰恰是要使神靈回歸於它應有的神聖地位。這一點與前述孔子對「人」的發現有密切的關係。
《論語·雍也》記孔子答樊遲問「知」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此語集中體現了孔子「神道設教」的社會教化觀念。「務民之義」,何晏《集解》:「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集解》:「敬鬼神而不黷」。這個解釋是對的。儒家的政治理念,其最終的目的在於教以人倫,導民至善,成就其為「王者之民」[16]。「務民之義」,即標明了此一目的。「敬鬼神而遠之」,則指出了達到此目的的教化之道。
所謂「遠之」,意在反對褻近鬼神。人神之間有分位,褻近討好以取悅於神靈,是一種功利的態度。周人雖以天或上帝為人間道德倫理之本原,然其「祈天永命」的態度,則是功利性的。一般百姓的宗教信仰,亦有很強的功利性。董仲舒謂「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17],即點出了日常百姓生活這種功利性的特點。民間一般的卜筮、祈禱、祭祀活動,其目的多在祈神邀福。中國古代社會的神靈信仰,是以天帝為至上神統攝眾神的一個多神的系統;社會每一成員,亦各依其在社會倫理關係中之分位差異,而有不同的致祭對象。《論語·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八佾》:「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祭有常典,位各有當。非其所當祭而祭之,名為「淫祀」[18]。淫祀的本質,是諂媚鬼神以求福報。人懷利益之心,用供奉財利一類手段,以求褻近取悅於神靈,實質上已將神靈降低為一種喜諂媚、愛財賄的功利之神,因而失去了它所本有的超越性和神聖性。是之謂「黷神」。「諂」,是就主觀一面而言,「黷」,是從客觀一面言。由諂媚褻近神靈,而必致於黷神,故為孔子所不取。與之相對,「遠之」,正是要把中國古初以來社會的信仰對象——天、神,擺回它應有的位置,重新確立起其神聖性的意義。
「遠之」,是從對象方面講,即要恢複信仰對象所應有的神聖性;「敬」,則是從主體方面講,其所關注者,在人內心的誠敬。「遠」與「敬」,猶一體之兩面,不可或分。《學而》:「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言喪祭之義[19],要在追思生命本原,以敦民化俗,成就德性。這「民德歸厚」之前提,則是內心之真誠與敬畏。儒家論喪祭,對親親孝心之誠敬十分強調。孔子祭必親與,祭神如在[20],所突出的,就是內心的誠敬。「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其意亦在於此。古人有天佑有德,鬼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此一觀念,雖對民間社會倫理秩序之保持有重要的作用,但其在實踐上卻易於引發追逐外力,諂媚褻近鬼神的功利態度,實無益於真正的信仰之建立。《論語·先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說苑·辨物》記孔子答子貢問死人是否「有知」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晩也。」這也可以印證,孔子對鬼神之「不語」、「遠之」的態度,並非否定鬼神,而是避免啟人外在追逐神靈福佑的功利心,喚回人對其自性、自心、自力的專註。孔子強調,為人當行人道,盡人事,確立內心的誠敬與敬畏以對越神明天道,而非僭越躐等,外在於人而褻近鬼神企慕天或天道。這使上古以來的天帝神靈信仰,發生了一種由外向內的轉變。
第三,因任傳統社會的禮樂教化方式而對其作出人文的解釋,以行其教化於社會生活。
一般的宗教教化,落實到實踐方面,必有自己的一套儀式儀軌系統。儒家行其教化,亦特別注重禮儀的作用。《禮記·昏義》:「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冠、昏,關涉於個人和家庭生活;喪、祭,關涉於宗教生活;射、鄉,關涉於社會生活;朝、聘,關涉於政治生活。「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在孔子之前,周代的禮樂文明,已經以一種完整系統的形式,運行於從個體、家庭、家族到政治、社會以至於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的是,這套禮樂的系統,乃由歷史傳統之延續而形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所本有,並非儒家另起爐灶的創製,亦非為儒家所專有。儒家所做的工作,是在每一個時代對它做出一種因時制宜的重建,同時,又著力於對此禮樂傳統作人文的詮釋,以建構其超越形上的基礎。《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易·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在儒家看來,那「察乎天地」的形上之道,與作為生活樣式之禮儀,同本於百姓日用倫理之常。故儒家既由社會生活之反思以建構其超越之理,同時又經由社會本有之禮儀形式,而施其教化的理念於民眾生活。
《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文字學的角度說,「禮」字之初文本與獻祭神靈、溝通神人的祭祀禮儀相關。[21]古時行禮,亦必有祭儀。是以古代社會的禮儀,與人的宗教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儒家於諸禮之中,又特別注重喪祭禮儀。前引《禮記·昏義》言儒家於禮「重於喪祭」。《祭統》:「凡治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中庸》亦引孔子說:「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都表明了這一點。禮或禮樂,是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樣式,具有移風易俗,潛移默化,化民於無形的實踐、教化功能。喪祭禮儀更直接關乎傳統社會的宗教觀念與神靈信仰系統,故尤為儒家所重視。儒家論喪祭禮儀,並不否定此喪祭禮儀所指向的神靈世界和信仰系統,同時,又通過一種人文的反思和義理的建構,來揭示其意義,引領其精神的方向,表現了一種獨特的接引神聖世界的方式。[22]
與前兩點相關,儒家對「禮」的反思與義理建構,亦使其發生了一種內向性的轉變。要言之,儒家謂禮之義非在祀神致福,而在於返本復始,追思並挺立人的生命本原;禮文乃稱情而立,根於人性,禮之本質及其發展之內在動源,實本乎文質之連續與統一;是以祭之義,必內求之於心,報本反始,由此上達契合於天地生命之本,以建立人之存在的超越性基礎。請略述之。
曾子以「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論喪祭之旨,儒家論禮所以成立之根據,復有「三本」之說。《大戴禮記·禮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天地為一切存在物生成之本原,先祖為血緣族類之本原,君師則為道德人倫創製之本原。從直接性上講,吾人之生命出於父母先祖,然原其本始,則必歸宗於天地之一本。而人之生命,又非僅僅是一種自然的存在,須經由人倫之創製,道德之養成,乃能得以實現,故「君師」亦得居「三本」之一。
此所謂三本,並非平列的關係。《禮記·郊特牲》論天子郊天之義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禮記·祭義》:「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古代社會,唯天子有祭天之權。天子郊天之祭,乃標示並賦予了祭祀以本質性的意義。在儒家看來,祭祀之要義,在於返本復始,追思生命之本原。而此本原之追蹤,則是通過「法祖而敬天」的方式,以親親為發端,循著由內及外,由近及遠,以上達契合於天地生物之本的途徑來實現的。
儒家反身據親親而追思上達生命之本原,其所論祭祀之義,乃由外向功利性之祈神致福,而轉為通過情感真誠之內心安頓以達天人之合一。《禮記·祭統》:「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即表明了這一點。「物自外至」,「物」指祭物。以求神致福為目的,所重者必在「物」及其外在的形式儀文。賢者孝子之祭,雖亦需有「物」,然其所重,卻在「自中出生於心」,「內盡於己」,「致其誠信與忠敬」,盡其內心之誠敬以契合於「道」。鄭註:「為,謂福佑為己之報。」「不求其為」,是特彆強調,祭祀非當以求福佑為目的。故祭非僅備物而已,其要旨在於盡其內心情感之真誠。
由此,禮之內涵乃被理解為本於情的文質之連續與統一。《大戴禮記·禮三本》:「凡禮,始於梲(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禮,有情有文,有義有數。文和數,指禮的儀文和形式。情是其內容,義言其本質。禮之「義」即表現並完成於此情文的統一與連續性中。《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觀殷夏(之禮)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是情文亦即質文。情或質,指人的自然生命;文,則指人文的創製。周世文明,兼綜夏殷而統合質文,故能成就一代文治之盛。「情文俱盡」,為禮之意義之最完滿的表現。從邏輯和結構的角度,可以把禮的內涵表述為質、文兩個方面的統一。從歷史發生的角度來看,禮「始於梲(脫),成於文,終於隆」,則表現為一個由質到文,由疏略而趨於繁縟的過程。一代之制,或有所偏,然其內容,要不外質文之互動互涵,二者猶一體之兩面,不可或分。孔子謂禮固代有損益,而後雖百世可知者以此。
質文互涵,「質」標識人的存在之自然的一面,「文」則表現為人的自然生命於其精神層面的開顯。儒家論禮之質文,曰「稱情而立文」[23],曰「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24],凸顯了情、質對於儀文的根本性意義。孔子自稱「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者」[25]言治道,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26]《禮記·禮器》說:「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前引《郊特牲》也說:「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要言之,復古、貴本、重質、重情,構成了儒家禮論和文化觀念的一個基本特色。而這個復古貴本,並非實質性地回到自然,其要在於「貴本而親用」。《大戴禮記·禮三本》:「大饗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梁,祭嚌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在這裡,禮文儀節及其倫理的規定乃被理解為人的自然生命存在(「質」)在其精神規定和人文自覺層面(「文」)的敞開與實現。周世信仰系統中「民彝物則」(禮儀、禮樂)本原於天的觀念,亦由而獲得了內在的人性意義。
以上三個方面的轉變,第一個方面關乎中國古代社會信仰系統之內在價值本原的建立;第二個方面關乎敬畏作為終極關懷之神聖性基礎的挺立;第三個方面關乎禮樂作為實踐性的社會生活樣式之重建。這三個方面,作為一個內在關聯的整體,其根本點,乃在於中國古代社會信仰系統之自律性德性基礎的建立。應當指出的是,這種轉變的契機,本潛存於中國古代社會的信仰系統中,但它作為這一信仰系統之內在真理性的自覺,卻使之發生了一種脫胎換骨性的本質轉變,此即前文所說「道德的宗教」之圓成。??
四.結語
綜上所論,儒學的思想作為一個自成系統的義理體系,與中國社會古初以來所形成的宗教信仰系統,又存在著一種密切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正是前述「轉變」所以可能的前提。這使儒學既能保持其作為一種哲理體系的獨立性,同時又能夠以其對社會信仰系統的詮釋和升華作用,施其教化的理念於社會生活。
帛書《易傳·要》篇記有孔子對弟子子貢解釋其「老而好《易》」的一段話,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儒家義理體系與傳統社會信仰系統的這種相關性:
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27]
在這段話中,孔子用「同途而殊歸」一語來說明自己與「祝卜」「史巫」之道的區別和聯繫。借孔子此語,我們可以對儒家思想與古代社會信仰系統之相關性做出一個確切的定位。
《易》本為卜筮之書。卜筮是古人測知神意以謀劃未來的一種方式,此祝卜和史巫之所為。子貢對夫子「老而好《易》」的不理解,亦由此而生。子貢提出的疑問是:「夫子它日教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何以老而好之乎?」[28]缺乏德行和智慧的人,只知外在地求神問卜,而不知返歸本心本性以決定其行止。在這一點上,子貢對孔子之教的理解並沒有錯。不過,孔子回答表明,在他看來,德性的成就和教化與一般百姓的宗教信仰之間,既有差異,同時又具有一種內在的關聯性,並非一種相互排斥的關係。
孔子並不否定古代社會以天帝神靈、祭祀禮儀、筮數占卜等為內容的信仰系統。儒家的形上之道,其至雖「察乎天地」,具有終極的超越性和極高的理想性,但同時又「造端乎夫婦」,為百姓所「與知」「能行」。春秋世衰道微,禮壞樂崩,道術為天下裂,孔子自覺承接擔當斯文,尤其注重於中國古初以來的禮樂文明的重建。孔子自稱「吾百占而七十當」[29],《易》本卜筮之書,孔子為之作《十翼》,並據以建立其「性與天道」的形上學系統,亦未否定卜筮對於民眾生活的意義。《荀子·天論》:「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亦表現了這種精神。這個君子「以為文」與百姓「以為神」,雖有不同的意義,但其對象和內容卻又是同一的。儒家形上學的體系,乃由對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及其信仰傳統的反思與義理建構而成,而非出於純粹的理論興趣。這與西方哲學那種「載之空言」式的體系建構方式是有根本區別的。此即孔子所謂的「同途」。不過,儒家的意義指向,卻與「祝卜」「史巫」所代表的社會信仰系統有本質的不同。「祝卜」「史巫」之道,意在褻近神靈,測知神意,其指向是功利性的。「我觀其德義耳」,「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仁[守]者而義行之」,「吾求其德而已」,乃由對神靈的外求而轉向於內,本內在德性的成就以奠立其超越性的價值基礎。孔子這裡所講的這個「德」或「德義」,指的是《周易》所包涵的義理或哲學的內容[30]。此即孔子所謂的「殊歸」。「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同途」,表明了夫子教化之道與社會信仰系統之間的一種相切和相關性;「殊歸」,則表現了孔子思想學說與社會信仰系統之間存在一種本質上的差別性或異質性。
孔子「同途而殊歸」一語所點出的這樣一個儒家義理體系與社會信仰系統之相關性和異質性統一的關係,對於我們理解儒家宗教性的特點,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和文化意義。
二者之「殊歸」的一面,賦予了儒學作為哲學的義理體系的獨立性特質。如前所述,儒學依其對殷周宗教系統之「連續性」、神性內在精神之理論自覺,建立其性命論和人性本善的觀念系統,確立了儒家內在超越的價值根據。其所建立的具有超越性意義的仁、道、天、天命等形上學的概念,並無人格神的特徵,其所重,在於經由德性的成就以體證天道,而非「以神為中心」來展開教義。對此,現代新儒家已有很充分的論述。依照田立克對哲學與信仰的區分,儒家思想的體系,是理性人文義的哲理,而非信仰義的教理,是哲學,而非宗教。故儒學之思想義理,可與康德、黑格爾一類哲學理論,同講論於現代大學的學術殿堂,而非如宗教神職人員之佈道,須限定於特定之宗教場所。
二者之「同途」的一面,乃使儒家思想對於中國社會生活及其信仰系統,具有一種內在的因應和切合性因而獲得了一種實踐和教化的意義。西方傳統的哲學,著重在通過一種理論和知識體系的邏輯建構,為社會諸文化部門提供某種普遍的「公度性」,其對社會生活並無直接的教化作用。中國東周時期之「哲學突破」,其中代表性的流派當為儒、道、墨三家。道家秉持自然的原則,其對禮樂文明之反思,深具批判性與消解性的意義,而缺乏肯定性的順適和建構。墨家延續了古代宗教觀念對人的功利性理解,以一種尚功用的精神,否定傳統的禮樂文明,同時也強化了人格神的天帝鬼神信仰。其對古代社會的信仰系統,適足以揚其所短而避其所長。唯有儒家秉持一種文質合一的精神,力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去反思重建西周以來的信仰和道德傳統。是以其思想義理,對傳統固有的宗教信仰系統,既有「殊歸」義的異質性之超越,又保持著「同途」義的相關性之切合。這種「異質性的超越」,使之具備了對社會宗教信仰系統之轉化升華的可能性;而這種「相關性的切合」,則又使之能夠對社會生活發生實際的影響和教化的作用。現代以來,儒學的思想傳統發生斷裂,中國社會雖不乏各種精妙的哲學理論,但其多由西方舶來,缺乏與社會信仰和民眾生活的關聯性,因而無法對社會生活起到提升和引領的作用。一方面是哲學理論的游談無根,另一方面是社會生活的無依無靠,當代中國社會之信仰的缺失,道德的失墜和墮落,蓋由於此。可見,儒學義理與社會信仰之「同與「殊歸」這兩個方面的關係,缺一不可,而其「同途」義的相關性一面,尤見重要。
「同途而殊歸」這樣一種關聯社會生活的方式,使儒學獲得了一種其自身獨有的文化和精神特質。前孔子時代的禮樂和信仰系統,具有普泛的社會意義,經由儒家形上學的提升與點化,其道德自律的基礎乃得以建立,其作為「道德的宗教」之意義,亦始得以圓成,因之而可大可久,構成幾千年中國社會之超越性價值與信仰的基礎。儒學的宗教性和教化作用,即體現於這種以「神道設教」的教化方式中。一般的體制化宗教,在信眾群體上有局限性,其儀式儀軌系統亦為特定的宗教和教派所專有,因而具有固定和排他的性質。而儒學所據以關聯於社會生活之禮儀及與之相關之信仰系統,既為社會所本有,並具施及全社會的普泛性,故其教化之所行,在中國社會,既最有普遍性意義,同時亦具有對其他信仰的廣泛的包容性。而儒學作為一種哲理體系對整個社會之持續的精神引領作用,亦賦予了這種信仰生活以更強的理性特質,而弱化了常常會伴隨宗教信仰而來的非理性的狂熱。這是儒家教化之異於西方宗教與哲學之獨具的特點。
[1]參閱李明輝《從康德的「道德宗教」論儒家的宗教性》一文的第二部分:「康德論『道德宗教』」,載哈佛燕京學社編《儒家傳統與啟蒙心態》,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參閱鄭開《德禮之間》第二章,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版。需要說明的是,鄭開教授認為周人所謂「德」,主要表現為一種政治語境中的「德」。這是很正確的。但同時也要看到,《尚書》、《詩經》和周代金文中都載有大量有關「德」的道德倫理意義的內容。「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降王祚於有德者,這個意義上的「德」,還主要是就道德倫理意義而言的,可以把它與維持王權國祚的政治指向相對區分開來。這「德」的內涵,不能僅從西方學者所謂「卡里斯瑪」的意義上來理解。本文主要是從這個角度借用鄭開教授「德禮體系」這個概念的。
[3]參閱同上書,第92-95頁;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第七章。
[4]《尚書·多士》、《召誥》。
[5]參閱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8頁。
[6]參閱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三章第一節。
[7]《論語·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就表現了這一點。
[8]《論語·堯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9]《禮記·中庸》引孔子語。
[10]帛書《五行》:「心也者,悅仁義者也。」「循人之性,則巍然知其好仁義也」。「源心之性,則巍然知其好仁義也」。「能進端,能終<充>端,則為君子耳矣……不藏尤<欲>害人,仁之理也;不受吁嗟者,義之理也……充其不尤<欲>害人之心,而仁覆四海;充其不受吁嗟之心,而義襄天下。而成<誠>由其中心行之,亦君子已!」(龐朴《竹帛<五行>篇校注》,《龐朴文集》第二卷,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8、144頁)
[11]參閱拙著《教化的哲學》「第四章 一、(二)」,第199-205頁。
[12]《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13]《孟子·盡心上》:「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14]《孟子·盡心上》:「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15]見《孟子·萬章上》。
[16]參閱拙文《「民可使由之」說所見儒家人道精神》,《人文雜誌》2013年10期。
[17]《漢書·董仲舒傳》。
[18]《禮記·曲禮下》:「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19]何晏《論語集解》:「慎終者喪」,「追遠者祭」。
[20]《論語·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21]參閱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第二章、二,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第六章、一,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版。
[22]參閱拙文《儒家的喪祭理論與終極關懷》,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2期。
[23]《禮記·三年問》。
[24]《禮記·坊記》。
[25]《論語·述而》。
[26]《論語·衛靈公》。
[27]廖名春《帛書〈要〉釋文》,見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頁。
[28]廖名春《帛書〈要〉釋文》,見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頁。
[29]見廖名春《帛書〈要〉釋文》,《帛書<易傳>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頁。
[30]說參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229頁。
來源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