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偉馳 | 天主教現代主義神學的演化
編 按
十九世紀末,在現代觀念的衝擊下,天主教內一批神學家開始引入現代聖經批評學和歷史主義觀點來研究教會史和教義史,但是這召來了教會的彈壓,現代派失敗。但是,現代性問題依然存在並且越積越多,從1930年代開始,新一代神學家開始成長,他們的神學思考彙集在「溯源運動」里,並最終匯入「梵二」神學。天主教現代主義的主力是法國神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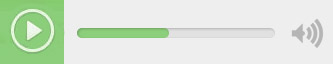
如果用新教面對現代性的反應模式「自由派-基要派」來看天主教,就很容易理解天主教神學的內部鬥爭了。一派傾向於適應時代,吸收時代文化(尤其哲學與神學),一派則執守傳統,依舊固我,不為時代所動。天主教內部的「改革派」可以有多種流派或標籤,如1890-1910年間的現代主義,1930-1950年間崛起的「溯源運動」(或「新神學」派),但它們的精神是相似的,就是用歷史批判方法來研究自家傳統,用現代文化處境中的現代人的世界觀來重新解釋傳統,激活傳統,使傳統能夠以新的形式「傳」下去。天主教內部的「保守派」也可以有多種形式或多種標籤,尤其是占統治地位的作為梵蒂岡官方意識形態的「新托馬斯主義」,其共同點是「守成」,要在現代語境中保留「原本」的「主義」,以不變應萬變,維護古老的信仰。如果說改革派容易被現代思潮同化,那麼保守派就容易走向僵化,成為新時代的「活化石」。在夾雜著一系列組織的、政治的、學術政策手段的鬥爭中,「改革派」和「保守派」各自遭遇了自己的命運。「改革派」先是被壓制,後是大放異采;「保守派」先是貌似強大,陣營鼎盛,最後卻走向了自我分裂,堡壘被從內部攻破。二十世紀天主教神學的基本演變線索,如著名神學史家克爾所說,「二十世紀天主教神學的歷史,就是試圖通過審查、解僱、開除來消滅神學上的現代主義——以及不能用這種手段壓制下去的問題重新湧現——的歷史。」[1]
天主教的現代主義發韌於宗改之後,鼎盛於1890-1910年代,出現了幾個代表人物和一批代表著作,但他們只享受了二十年左右的黃金時期,就被教廷給壓制住了,代表人物有的被開除教藉,有的被迫失聲,從學術界消失。但他們的影響一直潛在於新一代天主教神學家心中,只不過有的人迫於教會的壓力,不敢公開承認受到他們的影響罷了。
當然我們可以把天主教現代主義追溯到十八世紀,但一般提到的人物,只是德國的圖賓根學派,英國的紐曼等等。[2] 至於顯山露水的「正式」成形的現代派,則一般從盧瓦西(Alfred Loisy, 1857-1940)算起。盧瓦西的現代性體現在他試圖將對聖經的歷史批判引入天主教,使天主教聖經學現代化,以適應現代世界激劇地變化了的知識圖景。
給「天主教現代主義」或「現代派」下一個定義很困難,在教廷反現代派的過程中,雙方都沒有給出過一個嚴格的、清晰的定義。現代派不無委屈地認為,他們並沒有一個什麼現代主義系統,《放牧》(Pascendi)通諭中對他們的刻畫是不合理的。而教皇一方卻認為在現代派不成系統的手法背後,是他們對現代精神的頑固堅守。不過,雖然有這樣的困難,卻可以對雙方的差別作一個簡明扼要的斷言:一種持續了兩千年並且因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而強化了的世界觀,遇上了一種新近出現的歷史意識。[3] 其要害就在於,在自由派新教對傳統教義信念的堡壘發動攻擊時,願意向他們投降——這麼做時是以一種天主教的特殊的方式進行的。[4] 其核心就在於天主教內部的一批學者向新教釋經學「投降」,採納其歷史批判的方法來研究聖經,從而被傳統派認為危及了信仰。
現代釋經學一般認為是從德國新教開始的。賴馬路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 1694-1768)對聖經的歷史性做了具有摧毀性的考察,其著作死後才發表。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繼承了他的遺產,認為普遍真理不能是建立在歷史論證上的。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1874)在其《耶穌傳》(出版於1835-1836年)則顯示,新約中的耶穌基督的形象的真正價值在於其創造性的神話學。[5] 在法國的歷史批判成果,則有勒南(Ernest Renan)的《耶穌生平》。作為勒南的晚輩和學生,一貫被視為天主教現代派代表的盧瓦西(Alfred Loisy)就從德國新教釋經學學到了不少東西,將釋經學引入了天主教內部。不過,天主教現代派在將新教釋經學引入的同時,也有其自身的特色。相比於新教,他們更強調傳統的意義,不過跟以往做法不同的是,他們對之重新做了解釋,將傳統因素和實踐視為有效的象徵體系,他們為之辯護的基礎已是主體哲學,而非傳統的實在論,這導致了他們步新教的後塵,在信仰價值和事實價值之間造成了分裂。[6]
天主教現代主義首先和主要是從釋經領域開始蔓延,波及教義、教會制度、教會史、禮儀等領域,其代表人物主要產生於法國、義大利和英國。[7]
1907年7月,教皇庇護十世發布《可悲嘆》(Lamentabli sane exitu)諭令,以跟1864年庇護九世《現代錯誤學說彙編》一樣的格式,羅列了它所反對的65條論點——主要是從盧瓦西的著作中摘引出來的,並重申了教會官方的有關教導:上帝默示與聖經無誤性;關於啟示、信仰和教義的概念;儀式;教會憲章;基督教真理的不變性。同年9月教皇發布了《放牧主的羊群》(Pascendi dominici gregis)通諭。它系統地反對了《可悲嘆》中所說的各種「錯誤」觀點,用一個新詞「現代主義」稱呼它們。那些堅持這些錯誤觀點的人,從此就被貼上了「現代派」的標籤。
教皇通諭認為這些新的錯誤——「一切異端之匯總」——其根源在不可知論和宗教內在論(religious immanentism)。在宗教領域拒絕理性演繹,或者將宗教真理還原為情感和需要,被教會視為放棄了對基督教信仰進行理性辯護。同樣被拒絕的還有現代聖經批判學,以及要求改革教會結構的呼聲。作為一種對策,教會命令各神學院必須學習經院哲學和神學,對強對神職人員所寫著作的審查,建立監管機構,實際上建立了一套教會特務體制。
《放牧》通諭和《可悲嘆》諭令,將人們的焦點集中到了信仰與理性的衝突問題上。它們所包括的一些論點,在整個二十世紀都在討論,包括梵二會議之後。不過,很難說盧瓦西一個人就真的代表了教皇所譴責的論點,在它們背後還有不少別的持相似觀點的神學家。通諭只涉及所講問題的負面理解,點明了存在於傳統教會教義和現代哲學與宗教觀念之間的衝突。它並沒有解決如下問題:在批判性的知識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怎麼去正面地表達信仰。
導致某些書被放進禁書目錄、某些人受到紀律處分、有時某些人被開除的「現代主義危機」,對法國和義大利衝擊最大,也影響到了英國的某些知識分子。德國的天主教卻未受衝擊。因為早在梵一會議前後,教會早已將多林格爾(Ignaz von Dollinger, 1789-1890)和別的神學家逐出教會,德國神學被迫轉到了歷史學領域,尤其是教會史,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對爆炸性問題的探究。
在1790年法國大革命中高盧教會崩潰之後,法國神學家的起點是革命帶來的世俗化衝擊。勒南(Ernest Renan)在1863年發表其《耶穌生平》,它成了法國整個十九世紀最暢銷的書。勒南向其時代有教養的中產階級傳達了看似有理的耶穌和教會圖像,而擺脫了那些看來再也說不通因此遭人反感的方面。他的著作在由第三共和國發起的反對天主教教會的戰鬥中得到廣泛傳播。天主教神學被逐步地從巴黎大學和法國各學校中驅逐出去。直到1875年,教會才開始建立了一些天主教大學[8];數年之後,它們卻被國家強制重新命名為「天主教學院」。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學院里,第一批衝突出現在教會史領域,尤其是關於教皇制的開端和法國的地區、地方教會史的領域。值得一提的人物有杜切斯勒(Louis Duchesne,1843-1922),他想方設法逃避了教會的審查,以及巴蒂福爾(Pierre Battifol, 1861-1929),他失去了他的圖盧茲天主教學院院長的職位,他關於聖餐說的書被列入了禁書目錄。
天主教的聖經研究由於耶路撒冷聖經學院(Ecole Biblique in Jerusalem)的建立而得到了實質性的推動。與聖經學院創立者拉格朗日(Marie Joseph Lagrange, 1855-1938)相反,盧瓦西繼承的是勒南的聖經批判路線,雖然他拒絕了勒南的科學主義。盧瓦西因為認為聖經受到歷史環境的限制,而被迫辭去他在巴黎天主教學院的釋經學教授職位。1902年,他的著作《福音與教會》(L』Evangile et l』Eglise)發表了。哈那克(Adolph von Harnack)否定教會在傳遞信仰中的持續不衰的作用,盧瓦西反駁了他的這個觀點。盧瓦西的這本書為他贏得了「現代主義之父」的綽號。1903年他的五部著作被列入禁書目錄。在他用辛辣的反諷和高超的論證對《放牧》通諭加以還擊後,1908年他所有的著作都成了禁書。
盧瓦西並非孤軍一人在奮戰,與他處於同一戰線的還有哲學與宗教心理學家布龍代爾(Maurice Blondel, 1861-1949),在其代表作《行為》(L』action, 1893)中,他反駁了包括新經院主義在內的各種形式的客觀主義,表明知識和存在的啟示是跟主體性緊密相連的。在他看來,內在與超驗之間的對立在「行為」——「存在的自我實現」——中得到了綜合,在「行為」中,內在性揭示了自己即是超越的。布龍代爾的學生拉伯冬尼埃(Lucien Laberthonniere)甚至走得更遠,更強調宗教哲學內在性的一面。他說,一條宗教教義的約束力依賴於信徒在多大程度上將它消化成了他的個人生活法則。布龍代爾和拉伯冬尼埃都被指責為在搞內在論,被懷疑為現代主義。身為奧拉托利會友(Oratorian)的拉伯冬尼埃受到了來自教廷的警告。布龍代爾則由於是平信徒而避開了教會的審查。而且,作為人類有對面見上帝的天然渴望的重新發現者,以及在神學與恩典關係上有新見的理論家,他深刻地影響了導向梵二會議的神學,影響了呂巴克(Henri de Lubac)的「新神學」,影響了馬雷夏爾(Joseph Marechal),以及謝努(M. Dominique Chenu)和拉納(Karl Rahner)。
在英國,雨果男爵(Baron von Hugel, 1852-1925)作為一位獨立的學者,在那些同情現代主義的各國思想家之間建立起了通信網路。他能夠逃脫禁書目錄多虧了他的平信徒身份。相形之下,英國耶穌會士特列爾(George Tyrell,1861-1909)就沒那麼幸運了。他批判教皇至上和教皇無謬論是搞「中世紀主義」,反對教會的集權主義,反對認為教區主教僅僅只是教皇的代理或代表。他認為存在著一個「純粹托馬斯主義」,只不過它後來被「蘇亞雷斯主義」污染了。在《中世紀主義》一文中,他提出了教會得要面對的真正的問題:教會的治理、平信徒的尊嚴和角色,經驗和傳統與真理的關係問題。[9] 1906年他被耶穌會開除,並被教皇親自逐出教會。不過特利爾在英國教會中沒有激起什麼波瀾,因為英國教會向來保守,連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0-1890)的神學他們都難以接受,因此新的批判意識對英國天主教幾無影響。紐曼儘管先是在法國,後是在德國產生了影響,被譽為通向現代神學的橋樑,但他在自己的國家卻受到懷疑,儘管他在1879年被封為樞機主教。
反現代主義運動的最負面的遺產,乃是膽怯的心智對現代主義不加區別地一味斥責。它常常被用來掩蓋重要的新的問題。膽怯的精神們畏縮了,在反現代主義的避風港里避難去了。
盧 瓦 西
布朗(Raymond E. Brown)回顧了近代天主教對聖經批判學的態度演變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00-1943年,天主教保持傳統的對聖經的信仰態度,不允許對聖經進行批判的考察,因此是反批判時期;第二個階段從1943年開始到梵二會議,天主教逐步地有條件地接受聖經批判學,成立聖經委員會和研究所,開始准許學者採用批判方法論研究聖經;第三個階段是從梵二會議到現在。[10]
而盧瓦西正是在第一個階段前夕便開始了他的聖經批判,他於1902年發表的《福音與教會》轟動一時,引起了教會保守勢力的反對,導致了教會對聖經批判學的禁止,從而使得天主教在聖經批判學方面嚴重地落後於新教和世俗學界。
盧瓦西《福音與教會》標誌著天主教從傳統的釋經學向現代聖經批判學的轉變。早在巴黎的天主教學院(Institut Catholique at Paris)求學時,盧瓦西便已跟從著名的法國天主教教會史家杜切斯勒(Duchesne)學習,並在法蘭西學院聽前幾年才出齊了八卷本的《基督教的起源》的勒南的課。他亦在聖蘇爾庇斯神學院(Seminary of Saint Sulpice)聽當時法國天主教最有影響的釋經學家維高饒克斯(Vigouroux)的課,但發現它是字面解經,跟時代完全脫節,因此在勒南的啟發下,萌生了用新的釋經法來取代傳統釋經學的志向。在勒南和杜切斯勒的影響下,他深入地學習了德國聖經批判學。畢業留校後,由於他一貫的批判學的傾向,他講課的內容受到教會監聽,教學秩序受到打擾。1893年,盧瓦西只好澄清自己的觀點。他提出了五條:摩西五經並非摩西的著作;《創世記》前面的章節並非對人類起源的字面闡述;舊約和新約各卷並不具備同等的歷史價值,有一些「比現代歷史著作寫得還要鬆散」;「我們不得不同意包含在聖經中的宗教教義有真正的發展」;聖經跟其他的古典著作一樣,都有同樣的局限。[11] 巴黎樞機主教理查德(Cardinal Richard)看到盧瓦西的觀點後,強迫學校開除了盧瓦西。
於是盧瓦西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第二期,也是最富爭議性的時期。盧瓦西被學校開除後,被安排到了巴黎郊區的一家多明我會女修院任神父,給她們照管的小女孩們講課。這段時間裡他認識到,如果天主教要在人類歷史中佔有份量,就必須適應現代生活,象現在這樣抱殘守闕是不行的。於是,他將學術興趣轉向了在現代社會裡為天主教辯護,並研究天主教的歷史,以打下天主教神學改革的基礎。為此他雄心勃勃地開始了一個龐大的寫作計劃,它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當前的宗教理論,對普通的天主教理論和自由派新教都提出了批評,並借鑒紐曼的宗教發展理論提出了他自己的宗教構成說。第二部分討論歷史因素,共有五章,各章題目分別為:「以色列宗教」、「耶穌基督」、「福音與教會」、「福音與基督教教義」和「福音與公教崇拜」。它們讓讀者直接面對當今的問題和困難。第三部分先是過度性的一章,從歷史問題轉到現代處境,題為「公教教會的理智王朝」。接下來是綜合性的三章:「教義與科學」、「理性與信仰」、「宗教與生活」。後四章從未發表過。
1899年他因病退出女修院,同年底到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任教。在這裡他再也不受教會干擾了。但他覺得自己對教會負有「提醒」其適應時代的使命,因此仍然勤於著述,捲入現實問題。1902年,哈那克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被譯為法文出版,引起一些討論和爭議,盧瓦西正好寫到了哈那克書中談論的話題,於是從他的稿子中拿出一部分來,再加上對哈那克的回應,於同年十月出版了《福音與教會》一書。儘管這是一本站在天主教的立場上對哈那克的新教自由主義進行批判,並且為天主教進行辯護的書,但還是引起了對他一直不放心的教會保守派人士的不滿。那位巴黎樞機主教理查德於次年一月又一次跳了出來,譴責該書,並跑到羅馬去告「御狀」,要教皇也譴責它。教皇在十二月將盧瓦西的五部著作列入了「禁書目錄」,它們是:《以色列的宗教》、《聖經研究》、《福音與教會》、Autour d』un petit Livre,以及《第四福音》。盧瓦西通過巴黎大主教向教皇申辯,但教皇回復說,盧瓦西不是真心服從。1904年盧瓦西辭去了Ecole的教職,在一處小廬舍隱居,評註對觀福音。1907年,教皇的譴責終於下來了。教皇公布《牧養主的羊群》通諭和《可悲嘆者》的禁書目錄,譴責現代主義的錯誤。1908年三月,盧瓦西被正式開除教籍。
盧瓦西被教會開除後開始了他學術生涯的最後一個階段。1909年他被法蘭西學院聘為宗教史教授,這個位子是他原來的導師勒南空出來的。盧瓦西在這裡教書一直到1932年4月。退休後他回到家鄉村莊二十里外的Ceffonds生活,在接下來的七年里出版了八本書。1940年6月1日他去世,葬於香檳省的家鄉Ambrieres。只有三個人出席了他的葬禮,沒有舉行宗教儀式。他去世的時間算得上及時,因為幾天後德軍就包圍巴黎了。盧瓦西自撰的碑銘充滿了他一貫的文風:反諷與微妙。上面寫道:「阿爾弗雷德盧瓦西/神父/退出其神職與教職/法蘭西學院教授/求主憐憫一心想服從你意的僕人,不因其行而處罰之。」[12]
《福音與教會》一書引起樞機主教理查德的譴責,並引起爭論,但爭論時的焦點不是放在盧瓦西在跟哈那克商榷時說了些什麼,而是放在了對盧瓦西其人其書的貶低上,放在了盧瓦西的立場對傳統神學的含義上。保守派認為盧瓦西沒有站在傳統神學的立場上,沒有跟傳統神學保持一致,而是以現代釋經學作為方法來跟哈那克進行商榷,這在立場上就有問題了。確實,如果要當時的保守派來反駁哈那克,一定是會引用教廷公布的「永遠正確」的論點來反駁,而不會象盧瓦西那樣,同樣地用歷史批判學的方法「以毒攻毒」地反攻哈那克。
為什麼天主教如此不能容忍聖經批判學呢?這背後涉及到兩種世界觀的根本對立。
法國大革命以後天主教會外部的一系列的危機(如教皇國的消失、政教分離、民族主義、世俗化和理性主義),導致天主教的過激反應,在越山主義和回歸傳統的思潮的影響下,19世紀末出現了教皇永無謬誤論等加強教內中央集權的做法,在在都強化了天主教傳統的世界觀。這種傳統的世界觀,被著名神學家龍納根(Bernard Lonergan)描述為「古典世界觀」。它是這樣的:
它強調的不是事實,而是價值。它只能宣稱自己是普遍主義的。它的經典是不朽的藝術作品,它的哲學是永恆哲學,它的法律和結構是人類智慧與明智的沉澱。古典主義的教育是要人效仿模範,見賢思齊,領會永恆的真理和普遍有效的法則。[13]
而現代派的世界觀呢?如盧瓦西所說,「(他們)共有一個願望,要讓公教適應現時代的智性上的、道德上的和社會上的需要。」這種適應時代的需要使得對聖經進行歷史研究成為必要。可見,現代派對教會的理解是建立在歷史意識上的。真理是在歷史上真實的東西。這種歷史研究必然伴隨著相對性和發展的觀念,是認為只有「永恆的真理和普遍有效的法則」的古典主義者所無法容忍的。現代派的歷史意識不僅為古典主義者難以理解,也威脅到了他們的地位,因此二者註定要發生衝突。[14] 在古典主義者把持著教會權力的情況下,現代派註定要碰得頭破血流。
用另一個天主教學者的話來說,儘管現代派的一些元素(如歷史研究的方法、教義發展的觀念[紐曼]、以人的經驗與需要來為福音辯護)在以往的天主教神學裡面也有,但它們並沒有導致結構性的轉變。「但是現代主義並非僅是天主教神學中各種合法運動的總和,就象反現代主義並不僅僅是新經院主義支持的黨派反應一樣。早些時候無可指責的正統作家的反思路線,被發展成了他們根本想不到的結論(在布龍代爾那裡,根本就拒絕承認)。首先,在歷史的問題上,現代派的典型做法是排他式地只採用歷史科學資源來決定聖經及其他文本的神學意義,而不接受解釋過程中教會傳統起到的作用。他們不是說在神學裡歷史研究有重要的地位,而是說,歷史即一切。其次,在教義的問題上,現代派給人的印象是,教義只是一種運載工具,用來傳達某個特定時代對於神聖的回應的。適切於傳達一代人的時代精神的某個教義,到了另一代人那裡很可能就嚴重脫節了。他們不是說,在教義的明晰化過程中有歷史的層面,而是說,進化即一切。第三,在啟示的問題上,現代派看起來是在宣稱,基督宗教的整個解釋,可以歸結為人類精神(或靈性,spirit)對超越者的朝向(orientation)。聖經、儀式、教義、教會制度——都變成了象徵形式,是歷史中人類精神趨向於上帝的運動產生出來的。他們不是說,人對上帝的內在的服從是對神聖啟示的外在符號和教導的必要的補充,而是說,內在性即一切。他們得到了康德的主體主義和施萊爾馬赫的情感主義的幫助。在後者看來,不證自明的是,既然人類的知識只能局限於現象界,因此不能達到現象界之外的超越領域,那麼無論是上帝還是上帝行為的效果,都不是人類所能領會到的。人們並不總是能認識到,要被當作一個批判的歷史學家,贊同康德(或康德之後的)哲學很難說是一個必要的前提。」[15]
「反現代主義宣誓」
教廷認為是唯心主義、主體主義和實證主義哲學導致了「現代主義危機」,因此決定用「托馬斯主義哲學」來對抗它們。對於生於1890和1940年之間的天主教神學家來說,他們所接受的教會官方哲學與神學教育都是「托馬斯主義」。根據教會法,神職人員都必修用拉丁語講授的哲學與神學課程,這些課程都是根據天使博士托馬斯阿奎那的方法、教理和原則來思考一切。1910年,教廷要求所有的神職人員、教牧人員和神學院教師發誓反對現代主義(德國除外),直到1967年梵二會議後才被撤銷。這個誓言後來被稱為「反現代主義宣誓」(Anti-modernist Oath),其內容如下:
我,XXX,堅決擁護和接受由正確無誤的教會訓導權所確定、肯定及宣布的所有的和每一件事,主要是那些直接反對我們時代謬誤的教義觀點。首先我宣稱作為萬物的起點和終點的上帝,能確定地被天然的理性之光,由果知因地通過已受造的事物,即通過可見的創造之功,而能被認識,從而也能被證明。其次,我承認並把啟示的外部證明也就是神聖的行為——首先指奇蹟和先知預言——認作基督宗教神聖起源的確定表徵。我堅持認為,這些證明完全適合於一切時代和一切人——包括我們時代的那些人——的心智。第三,我還堅信,作為天啟之言的保衛者和教導者的教會,是由真實的歷史上的基督本人住在世間時親手直接設立的;它是建立在作為使徒品序(apostolic hierarchy)之王子的彼得(註:彼得原意磐石)及其直到時間末了的繼任人身上的。第四,我誠懇地接受使徒們通過正統教父所傳遞給我們的信仰教義,其意思與解釋永遠不變;因此我斷然地拒絕異端所發明的「教義進化」說,並不認為教會早先所持的教義的意思發生了改變。我同樣地譴責每一種謬誤,經由這些謬誤,傳遞給基督的新娘(指教會)並由她忠誠地守護的神聖寶藏(deposit,指信仰寶庫),會被某種哲學的發明或某種人類意識的創造物所取代,它們慢慢地由人的努力形成,隨後由無限的進步加以完善。第五,我堅定不移地堅持並誠實地宣稱,信仰並非從潛意識的深處涌發出來的一種盲目的宗教情感,因受到心靈的和受過道德教導的意志傾向的壓力而產生,而是理智對通過雙耳從外部收聽到的真理的真實的贊同,由於至真至實的上帝的權威,我們相信我們的創造者和主位格神所說過、證實過並啟示過的事情都是真實的。我亦恭敬地服從並全心全意地贊同包含在《放牧》通諭和《可悲嘆者》諭令中的所有譴責、宣布和禁令,主要是那些關於所謂教義史的內容。我同樣地責備那些認為教會所宣告的信仰跟歷史相抵觸,以及現今所理解的公教會的教義不能跟基督宗教更真實的起源符合一致的人。我還譴責和拒絕如下一些人的意見,他們說,見識更多的基督徒有一種雙重人格,一個是信徒的,一個是歷史學家的,彷彿——歷史學家持有跟信徒信仰相矛盾的觀點,或者寫下儘管沒有直接否定教義卻可由之推出教義是錯誤的或可疑的結論的命題——是合法的。我同樣責備那種評斷和解釋聖經的方法,它不顧教會傳統、信仰的類比和宗座的統治,而只去追隨理性主義者的意見,不僅非法地而且魯莽地堅持把文本批評當作唯一至上的準則。此外,我拒絕如下一些人的意見,他們認為不管誰教授神學史,或寫作這些事項,都要先放下任何關於公教傳統超自然起源的先入之見,以及為長久保持每條啟示真理所需的神聖幫助的諾言;此外還有每個教父的著作都只應該用科學的原則來加以解釋,而不管什麼神聖權威,對它們要自由地下判斷,就象研究世俗名著一樣。最後,我宣稱在一切事上都完全反對現代派所堅持的謬論,即神聖傳統中並沒有什麼是神聖的,或更糟糕,雖然有神聖的東西,卻是泛神論意義上的;所以那裡並沒有剩下什麼東西,只有赤裸裸的簡單的事實,也即普通的歷史事實,就是說,一些人通過他們的工作、技巧和獨創性,在隨後的時代繼續著由基督及其使徒開始的學派。因此,我最堅決地保持教父們的信仰,並將保持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口氣,熱愛那有著永不變化的魅力的真理,它存在於、曾經存在於並且將要永遠存在於使徒以來的主教傳承中;不是為了所堅持的可以變得更好或更適合於每個時代的文化,而是為了使徒們從一開始就傳布的絕對不變的真理可以永遠不被第二樣地相信或理解。
我發誓忠實地、完整地和誠懇地堅持這些信條,並無誤地加以監督,無論是在教學中還是在口說筆寫中都永不偏離它們。我如此許諾,我如此發誓,求主幫助我。
托馬斯主義24點
1914年,教皇在「自動詔書天使博士」(Motu Proprio Doctoris Angelici)中命令,神學院學生在學習神學之前,必須通過哲學考試,而哲學考試的內容被限制在24條托馬斯論點(Twenty-four Thomistic Theses)的框架之內。
神學史家克爾對這24論點有一個簡要的梳理和總結。他根據一般的看法,將它們分為本體論(ontology,又可譯為存在論)、宇宙論、心理學和神正論四部分,處理的主題分別是存在、本性、靈魂和上帝。
如果只是對24點做一個歸納,我們還是不能明白它們在當時歷史情境中的意味。根據克爾的分析,這24點是有針對性的,它們針對的是當時西方盛行的各種主體主義、唯心主義、情感主義、直覺主義、唯意志主義、表象主義、實證主義等各種思潮,而強調天主教信仰的理性特徵。24條全部訴諸理性,沒有提及聖經信仰,沒有提及三位一體、神人二性等神學教義,甚至連神正論中的苦罪問題都沒有提及,就是說,它們顯示,人能夠單獨地通過自然理性就證明靈魂的不朽和上帝的存在,人能夠如其所是地認識事物的本質(而不是象康德那樣認為達不到),天主教的信仰不僅不反理性和非理性,還非常理性——這本質上是一種實在論的形而上學。
托馬斯24點本來就是在反對教內教外現代主義中產生的,在成為天主教欽定的哲學教義之後,它就成了用了懷疑、審查、阻止、壓制現代主義的標準和工具。
那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天主教都有些什麼樣的官方哲學家和什麼樣的官方哲學呢?
當時在教會內學習的神學和哲學都是二手的拉丁文的教科書,學生上課不讀原始材料。所使用的教科書主要是由格列特(Joseph August Gredt, 1863-1940)撰寫的《亞里士多德-托馬斯主義基礎哲學》(Elementa philosophiae aristotelico-thomisticae,1899,1901),書中反對了對外部世界的懷疑主義和其他後笛卡爾哲學,還有比洛(Louis Billot, 1846-1931)撰寫的《道成肉身之言》(De Verbo incarnate, 1892)等神學著作。
而典型的托馬斯主義者是拉格朗日(Reginald Garrigou-Lagrange,1877- ),他長期在天使大學任教。他認為托馬斯的《神學大全》是不可超越的思辨神學成就,而通過十六世紀的一些托馬斯著作的評註者的評著來理解托馬斯是正確的途徑。他很少注意托馬斯神學的來龍去脈及其與同時代人的對話,而專註於托馬斯哲學中不變的命題真理,即「永恆哲學」。他的主要教科書是《托馬斯綜合》(La synthese thomiste, 1946)。他從分析常人的常識出發,得出了與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一致的「溫和的實在論」。那些不可知論、實證主義、進化論、德國唯心主義等,都是後來出現的違背常識的哲學,走上了歧途。那些不要托馬斯哲學的神學,都變成了主觀主義、內在主義、情感主義、實用主義一類東西,變成了一種經驗主義,而削奪了神學的「科學的」客觀性。[16]
「溯源運動」的興起
1900-1950年的天主教教會生活中,現代派思想家受到處分,並不意味著天主教神學的終結。在這一時期,除了新托馬斯主義繼續繁榮外,還出現了不少新的神學思潮,其中一個最突出的就是「溯源運動」(ressourcement)。他們繼承了教父哲學和經院哲學,同時又在新的語境中處理現代主義提出的問題,並深受他們影響。由於現代派被教皇譴責,因此新一代神學家不敢直接承認受到了他們的影響,但存在於他們之間的相似性是非常明顯的,這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採用了歷史的、批判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從聖經到神學史到教會史的一切領域。[17]
關於「溯源運動」,二十世紀末出版的「溯源運動:公教思想中的恢復與復興」叢書的篇首語有簡明精到的介紹。現翻譯如下:
本世紀(20世紀)中葉是歐洲社會充滿危機與變化的一個特別緊張的時刻。在這一時期(1930-1950),在歐洲天主教共同體內興起了一場宏大的理智的和靈性的運動,主要是為了回應處於這場危機核心的世俗化。這場運動從早前的神學家和哲學家那裡吸取靈感,如默勒爾(Mohler)、紐曼(Newman)、加代爾(Gardeil)、羅塞洛(Rousselot)和布龍代爾,以及一些文學家,比如佩吉(Charles Peguy)和克羅岱爾(Paul Claudel)。
被包括在這場運動中的學院哲學家群體伸展到了比利時和德國,體現在下面這些人的著作里:默什(Emile Mersch)、卡塞爾(Dom Odo Casel)、瓜爾迪尼(Romano Guardini)和亞當(Karl Adam)。但首先這段時期的神學活動是以法國為中心的。主要由福維埃爾(Fourviere)的耶穌會和索爾舒瓦(Le Saulchoir)的多明我會領導,法國的復興囊括了二十世紀天主教中許多最偉大的名字:呂巴克(Henri de Lubac)、丹尼埃婁(Jean Danielou)、龔加爾(Yves Congar)、謝努(Marie-Dominique Chenu)、波義耳(Louis Bouyer),及其同盟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
並非像傳言所說,這些神學家自覺地組織了一個「學派」:實際上,他們自己中間的分歧,比如在福維埃爾和索爾舒瓦之間,也是很重大的。與此同時,他們絕大多數人又都被一個雙重的信念統一了起來,那就是神學必須對當下的情境發言,而憑著信心如此去做的前提在於恢復教會的過去。換言之,他們清楚地看到,在後來所謂「與時俱進」(aggiornamento)中的第一步,就必須是「返本溯源」(ressourcement)——重新發現教會兩千年傳統整個兒的寶藏。比如,照呂巴克的說法,他自己所有的著作跟整個「基督教源泉」(Sources chretiennes)叢書都建基於這麼一個假定,「基督教活力的重新煥發至少部分地繫於重新探討基督教傳統在其中特別集中地表現了出來的時期和著作。」
總之,「溯源」神學家們的神學關係到「回到」基督教信仰的「源泉」,目的在找出這些源泉的意義和意味,以應對我們時代的批判性的問題。這些神學家所尋找的東西是一種靈性和理智的共融——共融於在其經典文本中傳遞給我們的最具活力時期的基督教,這共融將滋養、給力、年輕化二十世紀天主教。
「溯源」運動在梵二大公會議的文件中結出了碩果,深深地影響了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和信理部部長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樞機。
目前的系列就植根於這場二十世紀的神學復興,首先是在呂巴克和巴爾塔薩的靈性中體現出來的復興。與那靈性相一致,系列將「溯源」理解為重獲活力:回到源頭,目的在發展一種將真正地滿足我們時代挑戰的神學。因此系列中的一些特徵將是:
回到經典的(教父的-中世紀的)源泉;
更新對聖托馬斯的解釋;
跟二十世紀的主要運動和思想家對話,尤其注意跟啟蒙、現代性和自由主義相連的問題。[18]
可以說,「溯源」運動是一個上承現代派,下啟梵二的天主教神學改革運動。可歸到它名下的這些名字,可以說佔了二十世紀天主教大神學家中的半壁江山。
「一戰」對歐洲知識界造成了巨大衝擊。為什麼自詡「文明」「進步」「理性」的現代歐洲會發生如此的悲劇性事件?一時間湧現了不少對歐洲文明進行反思的「危機」著作,斯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1918-1922)轟動一時。1930年代,思想界空前活躍。知識分子都在思考歐洲文明的出路,從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到新崛起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而在不少天主教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歐洲的現代性亂象,其根源在於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人拋棄了基督教信仰,使得曾經在中世紀出現過的統一的基督教世界不復存在,使得基督對社會和文化的權威性統治不復存在。在他們看來,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現代性的後果,都是不好的,應該拒絕或者說超越現代性,回復到天主教的「基督教世界」。
在多種因素的湊合下,1930年成為了法國天主教智識生活的「黃金時代」。在文學領域,大名鼎鼎的有佩吉(Charles Peguy)、克羅岱爾(Paul Claudel)、伯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和莫里亞克(Francois Mauriac)。在哲學方面,儘管布龍代爾的主要著作已經完成,馬利坦、吉爾松(Etienne Gilson)、馬塞爾(Gabriel Marcel)和莫尼埃(Emmanuel Mounier)卻正在開始或擴大他們的影響。在神學領域,年輕一代的著作開始為世人所知:德日進、謝努、龔加爾、呂巴克、菲薩德(Gaston Fessard)。使這一代人區別於上一代的(尤其在神學和哲學方面),是他們積極主動地介入處於危機中的社會和文化。這使他們成為三十年後梵二會議的先驅。他們能夠做到這一步,是因為梵蒂岡與法國關係改善,政教關係理順,使年輕神學家不象前輩時不時發生國家與教會雙重身份撕裂的情況,發生良心上的折磨外,還因為自從1907年現代派遭到教廷譴責後,反現代主義的熱情逐漸熄滅了,而現代主義提出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反而積累得越來越多了,它們有待新一代神學家想辦法來進行處理。在1930年代的法國,重新開始有人撰文討論現代主義危機了。索拉格(Bruno de Solages)提出,現代主義危機只能通過提高教職人員的教育水平來解決。謝努則認為現代主義是「成長過程中的一場正常的危機」,是「基督教社會智性成長的一個正常的效果」,它為教會生活和神學帶來了豐富的成果,跟卡洛林復興以及十二、十三世紀經院哲學的情景類似。現代主義危機是由歷史意識導致的,而天主教神學應該在避免歷史主義和神學主義(theologism,認為教義永恆不變)這兩個極端的同時,積極地介入時代面臨的問題。
哲學家馬利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發動了一場托馬斯主義復興運動,在反對啟蒙主義的基礎上,在一戰後歐洲的「文明危機論」中,馬利坦是最早提出「新基督教世界」的政治神學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一位。馬利坦的著作激發了不少天主教思想家去思考,天主教究竟能為當代世界帶來一些什麼樣的具體的社會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差異。他們提出了諸多不同版本的「新基督教世界」,著力於基督教與現代性的關係,使天主教的救贖思想得以重新入世,而天主教過去很長時期內原本是消極避世的。
不過許多人還是不敢發表其研究成果,因為羅馬檢查官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還是懸在他們頭頂上呢。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4)的對進化論的宏觀思考就在這種情景中受到了有保留的對待。他的研究成果只能在死後出版。
「一戰」後德國也發生了類似於法國「天主教復興」(renouveau catholique)的情況,也經歷了一場文化人的大皈依,不少人奔到了教會這裡,這段時期心智最宏闊的天主教思想家是瓜爾迪尼(Romano Guardini, 1885-1968)。耶穌會中的兩兄弟,拉納家的雨果(Hugo Rahner, 1900-1968)和卡爾(Karl Rahner, 1904-1984),他們談論的許多話題影響到了梵二及其後。雨果在其《教會的象徵》(Symbole der Kirche, 1964)一書中,揭示了在傳遞信仰之積澱中象徵起到的作用,他的另一部著作《基督教解釋中的希臘神話》(Griechische Mythen in christlicher Deutung, 1945),運用赫拉斯(Hellas)的例子和教父神學來說明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宗教的相遇。他這麼做是要在基督之光里找回前基督教的關於上帝的智慧和知識。卡爾則成功地挑戰並打破了新經院主義語言和概念傳統。把他稱作海德格爾的徒弟(拉納確曾在海德堡跟從海德格爾學習),並沒有正確地刻畫出他的哲學方向。拉納思想的主要靈感和出發點來自於他的修會(耶穌會)的兩個神學家,羅塞洛(Pierre Rousselot, 1878-1915)和馬雷夏爾(Joseph Marechal, 1878-1954)。儘管他從沒有跟從他們學習,他們的著作卻開闊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用一種跟活生生的現代思想緊密相連的方式來解釋阿奎那文本的可能性。在這裡,又可以看到布龍代爾的進路在起作用:在人們對自我實現的渴求中,辨認出一個超越的根基,因此辨認出他們跟神聖啟示的隱藏的關係。卡爾拉納的思想有其靈性傳承,那就是對恩典經驗的肯定。其神學的結構性的時刻是從靈性傳統及其教父的、中世紀的和依納爵(耶穌會創始人)的解釋中衍生出來的。將傳統整合進他的神學,解釋了為何他的著作被廣泛地接受,尤其是他的22卷本的《神學研究》(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1954- )。他的國際名聲引起了那些更植根於經院主義方法的同事的懷疑,他們向羅馬打小報告,羅馬有人想要把拉納從梵二會議顧問的位置上拉下來,但他們失敗了。卡爾拉納還認為天主教教會有改革的必要——在這一點上他跟他的同事巴爾塔薩(Hans von Balthasar of Basel)是一致的,後者在1955年離開了耶穌會。巴爾塔薩也是受到了教會高層的懷疑,這主要是因為他在《拆除堡壘》(Schleifung der Bastionen,1953)一書中呼籲教會擺脫自我隔離。巴爾塔薩卻寫了九卷本的巨作《榮耀》(Herrlichkeit,1961-1987),它是一個「三部曲」,分別為神學美學、神聖戲劇和邏輯,它們構成了一個首尾一貫互相補充的大綜合。巴爾塔薩的作品受益於來自法國神學的靈感,它是由呂巴克引薦給他的。巴爾塔薩不僅是一個作家、靈性導師和佈道者,還是溝通法德兩國智性文化的橋樑。在其生命中最好的年份里,總是有一抹懷疑的烏雲懸浮在呂巴克、拉納和巴爾塔薩這三個人的上空。不過,最終結果卻是拉納成了梵二會議的神學顧問,而呂巴克和巴爾塔薩成了樞機主教。
簡要總結
1910年代初天主教現代派被教會高壓人為地壓抑下去後,它的精神並沒有消失,反而通過各種渠道(如個人交往、著作流傳)曲折地影響到了年輕一代的神學家。而被教會通過種種組織和政治手段強行灌輸的新托馬斯主義,內部充滿了爭議,發生了分裂,最後被歷史批判性從內部被攻破了。「二戰」後,隨著世界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教會的「中世紀主義」確實再也難以適應時代,在1930-1950年蘊釀力量的以「溯源運動」為代表的年輕一代神學家,終於在1962-1965年梵二會議上佔據了主導權,使該次會議成為最具有改革開放精神的一次會議。從此之後,新托馬斯主義極大衰落[19],神學邁入了多元主義時代,各呈精彩,不再定於一尊。現代主義-新托馬斯主義-新神學,可以說構成了二十世紀天主神神學思潮演變的主要辯證運動。
注 釋
[1] Fergus Kerr, Twentieth-Century Catholic Theologian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4-5.
[2] 關於以法國拉蒙尼為代表的第一波自由派、以德國默勒爾和多林格爾為代表的第二波自由派、以盧瓦西為代表的第三波自由派的「三起三落」簡史,可以參看利文斯頓,《現代基督教思想》(何光滬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10章。
[3] Bernard B. Scott, Introduction, xxvii-xxviii. in: Alfred Loisy,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Fortress Press, 1976.
[4] Aidan Nichols, Catholic Thought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Gracewing, Leominster, England, 1998. P.83.
[5] 同上。萊辛和施特勞斯的著作均已有中譯。
[6] 同上,pp.83-84.
[7] 以下關於「一戰」後天主教神學發展的內容參考了:Victor Consemius, 「The Condemnation of Modernism and the Survival of Catholic Theology」,以及Joseph A.Komonchak, 「Returning from Exile: Catholic Theology in the 1930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Theological Overview, ed. Gregory Baum, Orbis Book, Maryknoll, N.Y., 1999. pp.14-26, 35-48. Mark Schoof, A Survey of Catholic Theology 1800-1970, Paulist Newman Press, Paramus, N.J. N.Y., 1970. pp.93-121.
[8] Bernard B. Scott, Introduction, xvi. in: Alfred Loisy,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Fortress Press, 1976.由於天主教教育的長期中斷,法國神學和釋經學要落後於德國。從法國大革命到1875年的同一時期,在德國,新教神學和學術在德國大學裡佔有顯要的位置,用現代批判工具來對聖經做歷史研究,在德國是合法的。同一時期的法國並非如此,人們對聖經批判學要麼一無所知,要麼持拒絕態度。這可以解釋為何盧瓦西的聖經批判學在法國教會人士眼中顯得很「另類」,引起了軒然大波。
[9] Fergus Kerr, Twentieth-Century Catholic Theologian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5-7.
[10] Bernard B. Scott, Introduction, xi-xii. in: Alfred Loisy,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Fortress Press, 1976.
[11] Bernard B. Scott, Introduction, xix. in: Alfred Loisy,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Fortress Press, 1976.
[12] 關於盧瓦西葬禮的情況及墓銘的分析,可參:Marvin R. O』Connel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atholic Modernist Crisis,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C, 1994 , 「Prologue」, pp.1-4.
[13] 轉自Bernard B. Scott, Introduction, xxx. in: Alfred Loisy,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Fortress Press, 1976.原文出自:Bernard Lonergan, Method in Theology(N.Y.:Herder and Herder, 1972),p.301.
[14] Bernard B. Scott, Introduction, xxx. in: Alfred Loisy,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Fortress Press, 1976.
[15] Aidan Nichols, Catholic Thought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Gracewing, Leominster, England, 1998. pp.84-85.
[16] Fergus Kerr, Twentieth-Century Catholic Theologian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p.11-16.
[17] Bernard B. Scott, 「Introduction」, in: Alfred Loisy,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xxxi.
[18] 可見於「溯源」叢書中任一本書的扉頁,如Henri de Lubac, The Discovery of God,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6.
[19] 關於新托馬斯主義在現當代的流派分支和發展趨向,可以參看筆者「現代托馬斯阿奎那研究」一文,載《哲學門》總第17輯(2008),亦載於筆者《彼此內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一書。
因篇幅限制,本文略有刪減!
原文(完整版)發表於《宗教與哲學》(第三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宗教哲學茶座」經編輯部授權轉載,欲轉載煩請註明「宗教哲學茶座」微信號:zongjiaozhexuechazuo!
推薦閱讀:
※現代快報
※Jennifer McChristian 美國現代印象派女畫家
※視頻教學《現代探戈花樣》(全集)
※麥克法蘭 | 現代世界的誕生2:種姓和階級
※2015下半年新款現代簡約卧室設計效果圖大全 流行卧室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