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隨筆|卓梅森:莆田龜山寺生活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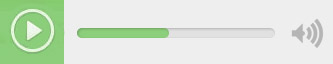
莆田龜山寺生活筆記
作者:卓梅森
自然篇:
白雲無住山藏寺 明月常圓佛在龕
入住龜洋古剎前,遠望山頭沒在雲中,卻沒想到,山上已下了陣瓢潑的大雨。這會,我站在寺院的高處四望,天藍,雲團正如大部隊在山頭上行軍轉移。在這氣候多變的颱風季節與陰晴無常的夏秋之際,白雲無定,不住地掠過寺頂。
龜洋古剎是福建莆田四大叢林中唯一頗得「深山藏古寺」畫意的大寺。一山欲開,眾山急圍。人們不論站在山下的什麼角度,都看不到它的片瓦角檐,因此即是本地人,也很有不知山寺方位的。山掩雲遮,為山寺提供了超拔塵世的天然屏障。「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唐詩,是山寺絕好的註腳。
中午晴亮,午睡起來,卻覺涼風推窗,對面的山頭正一座接一座地沒入雲團。白雲蒼犬,氣候的急變,襯照著古寺的寧靜與悠久。
上山的第二天是立秋。晚上在陽台上乘涼,月正明。風雲無常,月圓有常。龜山立寺千有餘年,明月缺而復圓,佛像暗而復亮也有上萬次了。寺院寬敞,僧人只要抬頭,眼中有月常圓。「明月常圓佛在龕」,有佛在胸心澄明,心如靈鏡台,若能勤拂拭,無月,心也亮堂。
半掩半敞的寺門,若隱若現的佛像,亦老亦少的僧人,青綠的松柏,凝定的山形,變幻的雲影,等等,正一道描寫著古剎的全景。
歷史篇:
三紫凌雲寺凌紫 龜洋積霧僧積洋
「峰高三紫,微塵不著人間」,龜山寺高據於三紫山與龜峰拱衛的山坳。三座紫山聯合行動,壁起於盆地華亭鎮的北沿。雨霧天氣,以三紫山為屏幕,大塊的雲團或呈縱隊直上,或繞峰腰橫起,峰靜霧動,山青雲白,為「莆田二十四景」之「三紫凌雲」。外三紫而內龜山,談三紫山必談龜山寺,正是山水與人文雙贏的局面。
天下名山僧佔多,九世紀初,祖師踏遍了莆田諸峰。他在認真進行差額選舉後,決定佔據這個最缺乏「位置經濟」的山頂盆地。祖師是為了修行,才到了這個離人很遠而離天很近的地方。祖師目光不凡。佔據了這個天盆,就佔據了俯賞「三紫凌雲」的自然美的制高點,就佔領了一個「泉可飲田可耕」的潛經濟開發區。不少大寺雖有盛名,但天生不足,其環境價值實在不能高估。寺廟無常,僧俗無常,只有自然永恆。依附山水,才能獲得原生態的氣質與純天然的風韻。
「三紫三山三及第」,落榜的三才子隱居三紫山並自封三及第,死後為三山神,因不斷抬高驚動天庭,終於被砍落三個山頭,成為山下的三個村莊。與三紫山同有凌雲猛志的,是龜山的開山祖師與傳承衣缽的歷代高僧。在只有羊腸小道的漫長年代,草木封山,蛇獸攔路,山上不產建材,一磚一瓦一石一木,包括重逾千斤的大石槽,無一不是從山下肩挑手抬,一步一步上到山寺的。能把一座廣達數百屋舍的大剎抬上山來,能無凌雲壯志嗎?說是肩挑手抬,也許太過平淡,也許難以置信,於是便有了「唐井吐杉」與「石鴨上山」等建寺傳說。至今龜山多雨霧,也不妨解作它的空氣中的汗水含量太多所致吧。
「龜洋積霧」與「三紫凌雲」並稱。山頂多霧,山盆就更易積霧了。二十年前,我雨後登山,剛進入龜洋,就落入霧中。我在前頭急跑,霧在後面徐趕。我進了寺院,整個平洋隨即淹沒在濃重的霧水中了。只要是陰雨天,總會演出「龜洋積霧」這平常又壯美的景觀的。
自然是偉大的,有人類生活的自然尤其偉大。一千年前,紆徐穿行在龜洋雲霧中的僧俗竟多至千人;五百年前,在雲霧中隱現的灰色人影也多達五百。寺連成村,衣連成霧,但依舊是山一般的寧靜,水一般的清幽。自然的荒涼之氣,僧家的脫俗之氣,渾然一體。近代,以雲霧為通道,由山入海,龜山的僧人與謀生的福建移民一道漂洋過海,於今在南洋積聚了不少的僧才。當然,除了盛期,其他階段積於龜洋與南洋的僧人不會太多,但古剎能綿存千年,大約總有一些僧人苦渡於霧底洋中的吧。
現實篇:
既出家三餐可飽 如無事一錢難得
寺院樸素的不止是灰色的僧衣,寺內的伙食也是簡單的。同事在吃第一頓飯時就問寺內有無更好的食物。幾天中,早晚吃稀飯,配一個鮮菜,外加咸蘿蔔、腌芥菜及炒花生。午飯稍好,蒸乾飯配青菜豆腐湯,偶有興化米粉與麵條。都是南方典型的飯菜,菜多是寺內自產,稻米過去也是富餘的。總體上看,寺院伙食高於人民公社時代的標準,但低於目前多數農家的水平。
一僧持雙木敲畢,另一僧舉木槌捶打銅牌,便是通知大家吃飯了。敲鐘而食,大鍋吃飯,有點像古時貴族之家的鐘鳴鼎食。每次到食堂,已有僧人寺工在盛飯了。有些人大概就是等著吃飯的,晚去者或有少食之憂,不過幾天中,還很少發現有誰因遲到而沒飯吃的。寺里雖有小賣部,但品種不多,僧人口袋中也沒多少余錢。
雖然水泥路直通山寺,但香客少,緣金不多。寺屬田產應不下數十畝,寺內勞力少,多請山下農民耕作。近十年來,農產品價賤,僱人已不合算,觸目所及,田野儘是綠草。除了一年收十餘擔的茶葉,加上城內幾家店面(海外下寺為祖寺購置的)能收些租金外,古寺已無其他收入了。問過寺內僧俗,說是除了出工每天有6元錢,平時就不再發薪了。傳統的寺風是一日不耕,一日不食,一聲鋤頭一聲佛,農禪結合振宗風。而今已進入工商業為主體的社會,寺僧除每日做課外,出去幹活的似已不多。因此,三餐雖可飽,消費談不上。好在寺僧很少下山,購物慾望不強。
不過作為整體單位,數十年來山寺也是與時俱進的。二十年前就拉上了電網,照明電路密布。煮飯既有灶膛與大鐵鍋,也有煤球爐與電飯煲。既保留了傳統的石杵臼與大石磨,也購置了碾豆機與打面機。自來水供應充足,洗澡用上了太陽能熱水器。程式控制電話現有四部,在山上也能收到移動通信的信號。彩電架上了天線,能接收央視、省台與市台,甚至在互聯網上也能查到龜洋古剎的簡易網頁。
禪思篇:
鐘聲陣陣醒迷夢 山色重重見本真
夜裡3:30,我在寺院客堂內被一陣響聲驚醒。玻璃窗震顫著,我起身貼在門板後聽了一陣,隱隱覺得聲音發自這座大剎,卻不明白深夜為何有這種聲音。早飯後一問,才知寺內僧人每夜4:00做早課,3:30就開始擂鼓。次晚7:40,我循聲望去,遠處鼓樓三層上有一僧人正對著豎立的大鼓敲打;10分鐘後,近處的鐘樓繼之響起了巨鐘的噌吰。這是在催僧人睡覺了。不過直到9:00我睡前,鐘樓內的電視還開著,鼓樓也還亮著。當然,明晨那裡仍會準點響起鐘鼓的,全體僧人也都會參加早課的。
「鐘聲陣陣醒迷夢」,夜鍾確能把人喚醒,但把寺僧從俗世中喚上山寺的又是怎樣的鐘聲呢?我問剛上山月余的小許,你只有一個兄弟,你又是家中長子,父母怎麼捨得讓你出家呢?「父母都是信佛的,我想進寺門,他們不會阻攔的。」小許有些靦腆地拿出一張字,說是自己悟出來的。紙上寫著人生「五大煩」,有父母、兄弟、夫妻等。錯別字不少,不過寫得認真,小許說他讀到初中。他又從床頭翻出幾本廣化寺印刷的小本本說,將來想寫一本書,書名想好了,叫《人生的懺悔》。不知道他要懺悔什麼,但自幼隨父母出入寺門的他,心裡大約是有鐘聲的。
我數了數,這龐大的寺院,只有十個僧人,包括長年常住寺內的寺工,不過十五人。據寺工說,現在有勞動能力的壯丁是不願進寺院的。看得出,有些僧人的身體甚至精神是不太健全的。我佛慈悲,給他們提供了個去處。不過,那位老僧七十多歲了,還頗有神采。據說,他原籍江口,家裡條件好,有出國的機會,卻在這裡一呆數十年,他到底為何出家,同樣在這十多年的老寺工也無法理解。文革前與老僧一同在山寺出家的七八十人,其中不乏能文能武的,他們選擇了出家,選擇了古剎,應該是受到深山鐘聲的召喚吧。
還有一個中年僧人,他出家的故事廣為人知。故事的模式在文學中是常見的,男女相戀,女方父母卻硬是把女兒另嫁,於是這對青年以出家的方式進行抗婚。比起以死抗婚,這不算剛烈,但中華文化的博大正體現在,不為禮教所容的人,還有佛教等途路可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佛門的慈悲正是在世俗的冷酷處體現出來的。而寺工在閑談中,還透露出故事鮮為人知的一面。女方當年也被迫出嫁並生有兒女,男方在寺門有了地位後,用重金把女方買進了尼姑庵中。敢情,這寺院的鐘聲中,也有對俗世的抗爭之音,甚至有兩心呼應的韻律。
一些文人,喜用成語詞藻把古剎包裝得金碧輝煌、活色生香。一些僧侶又好用渺茫的仙跡與無稽的傳說把寺門神化得煙繚霧繞、神秘莊嚴。許多小年輕,卻又不屑家鄉的寺廟,總是貴遠賤近、厚古薄今。在認讀楹聯時我還發現,寺內名聯的作者竟多是寺外名人,如明代國師陳經邦與清未莆田名人張琴。也許佛學無界,覺悟者不必常住寺中吧;也許寺外文士眾多,與山寺保持距離者更能做詩意的想像吧。但禪悟不必定要有文學的外衣,何況普通僧人的真實生活是沒有太多詩情的。其實禪宗高僧自有「呵祖罵佛」的反偶像之舉,他們視佛像如乾屎橛,甚至認為該劈成柴塊燒飯。心即是佛,佛即覺悟,佛學早已是最具實用理性的中國化西學了。
當然,民間需要偶像也是樸實的要求,禪學理念對於百姓不免太抽象太唯心了。觀念需要佛像來體現,僧尼需要寺院來食宿,信徒需要菩薩來關懷,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龜山無言,土壤磚紅,雜草潮綠;古剎不語,桌案蒙塵,佛像褪色。木魚聲,課誦聲,天明,層山淡入眼帘。寺院的一切,呈現著自在的面貌與本來的心性。「山色重重見本真」,穿過重重山色,穿過殿廊樓閣,走進寒磣的僧舍,便能見到僧家的家常境界甚至是情愛境界。
經濟篇:
天上樓台世上寺,雲中田園月中香
在底下望著山峰想像或登上山寺後回味山景,「天上樓台」確是頗有詩意的。今人乘車輛從鎮中心急馳半小時,就進入高在雲端的「天寺」了。如今的龜山寺,路亭,佛塔,門樓,墓園,寺院,間插著遠山與近田,水泥路的軸線一脈貫穿,構成了長達數里的景深。但置之於眾多名勝的旅遊網路體系中,或者置之於各大寺廟的人氣指數排行榜中,龜山寺顯得是這樣的荒涼與清淡。雖然僧人出家有些是想避世的,但交通發達的香火就旺盛,香火旺盛的就後繼有人,人群密集的渡世就便利,這在佛界也是明了的啊。可見,宗教市場也是需要基礎設施與普法環境的。
如今,藉助現代交通工具飛遍全國乃至世界的遊客,借交通工具之力輕鬆上山,在審美疲勞之餘,在美食膩煩之後,要給山寺一番地方保護主義的過獎,或是對山寺評頭論足妄貶一通,都是不費多少力氣的。但在二十年前,僧俗在從天上拋下的羊腸小道上勉強駐足,大喘粗氣時,情形就不太相同了。口乾舌燥,草割蟲咬,腳酸腰痛,然而「去天上的路」卻是山重水複,沒完沒了。饑渴,勞累,由足底到額頭,由五官至神經,全身心地感受疲憊。每個上山的遊客,都要經過這番徹骨的考驗才能享受山寺的休憩與清涼。作為會新陳代謝的僧人與會化學反應的寺院,要在山上養生長壽與保存光大,就更為艱巨了。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南洋老僧定光就是在回祖寺的登山途中累倒,而在去世前發願捐巨資開闢盤山公路的。
詩境中的「天上樓台」,終究是現實中的「世上寺」。山高霧重,浸泡在霧裡的山寺的一切,都更加容易霉變。門窗數日未開,客堂里就鎖了滿屋的腐味。太陽一出,寺院內的兩大石埕上都曬滿了草席。寺院多為土木結構,若無僧人勤快地洒掃擦抹,梁木牆壁朽化剝落的進程就更會加速了。對此,鍍金的菩薩也是無能為力的。要保鮮物品,還是要靠寺產,靠經濟力的支撐的。好在祖師選中的這個山盆,面積大,水源足,種植小麥、大豆、紅薯不成問題,就是南國第一作物的水稻也能種上幾十畝。牛耕人播,秧綠蛙唱,居然一派水鄉景象。在農業社會中,既能自給自足,又不需納稅,山寺簡直是世外桃源了。
山高,霧重,氣涼,更妙的是,文人眼中「龜洋積霧」的景觀,竟然正是高山發展茶業最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八閩通志》說「龜洋山產茶為莆之最」,《興化攬勝》也說「無了禪師來龜山開山,辟茶園十八處」。明代月中禪師主持古剎時,也是依仗茶業再次振興的,此時龜山茶業之盛,據說更甚於唐。名為「月中香」的茶葉年年晉京,成為貢品。唐代政策開明,經濟貿易發達,茶葉作為重要產品給山寺帶來巨大的收益。明中後葉,商品經濟有很大的發展,更給龜山寺帶來了重興的機遇。偏僻的龜山寺能歷千年而猶存,大約是離不開茶業的。在小農經濟的封建時代,山寺倒是發展出了一種與商業相結合的集體經濟。僧家經營茶業,有搞雙職業之嫌,但禪學講究在生活中悟道,耕禪並重,生產學佛兩不誤,既促進文化品種的多元化,又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有益而無害。強勢文化往往借強大的經濟羽翼以行,佛教文化作為一種上層建築,寺里和尚作為宗教職業者,沒有經濟基礎的平台,怎能施展「佛光普照」的法力?山寺,畢竟在世上,在人間。何況,龜洋山高客少,進行生產自救,以茶養寺,以農體禪,總比當閑和尚、乞食僧好吧。
悠揚的鐘聲穿越千年,濃醇的茶香飄散千年。龜洋古剎,終於奠下了莆田四大叢林之一的地位。當然,封建社會興亡無常,山寺也不能長盛不衰,但香火不滅,寺脈未斷。近代,龜山和尚向南洋發展,較早介入了國際宗教文化市場。依仗南洋的經濟強援,祖寺不但修葺一新,而且在高山頂上空前地建起了耗資百萬的閩中第一石塔。這功果,應算是一千年來經營茶業的思維慣性種下的業報吧。
趨向篇:
山水起伏寺浮沉 敢問僧家何處去
三紫山脈裹挾著龜峰,向著仙游永泰德化等縣境疊進。強烈地震帶上的三紫山,至今在板塊擠壓拉扯中升沉。狂風剝蝕,暴雨沖刷,千年不休,使山寺總是處在修建與傾圮的循環中。而對山寺影響最深的,還是社會帶來的地震與風雨。
創建二十餘年,龜山寺就遭遇了「唐武滅佛」。隋唐佛教傳播極廣,寺多僧眾,到了「天下十分之財,而佛有七八」的程度。皇帝不得不下詔廢佛,拆毀寺廟,勒令還俗。史載,武宗滅佛,僧尼26萬還俗,釋放寺院奴婢15萬及被寺院奴役的農民50萬,沒收良田幾千萬頃,減輕了國家和百姓的負擔,增加了幾十萬人的勞動力。但應具體分析的是,龜山寺開發的是荒山野嶺,且能以農業自力更生,較少佔用國家與社會的資源。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中豈容異類?於是地動山搖,浪卷舟翻,寺毀僧散。直到次年宣宗即位,恢復佛教,山寺才得以恢復。
文革前到過龜山寺的老人都說,食堂里坐滿了和尚。但文化革命的徹底程度是史無前例的,生長千年的杜松砍倒了,保存千年的佛像砸碎了,經營千年的茶園沒收了,只要山下還有家,哪怕是七八十歲的老僧也趕回去了。山下的中學甚至入主佛寺,辦起了不農不讀的中學。撥亂反正的新時期,不僅是科學的春天,也是宗教的春天。百廢俱興,山寺修復,規模倍增。
今天的宗教政策漸顯理性,但寺里的僧人卻降到了低谷,僅十人左右。寺工解釋說,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丁稀缺,幾家願意讓男人出家呢?僧源的減少以及素質的降低,無疑地約束了僧徒規模的擴展。但制約山寺的因素何止是「計生」?
全球經濟一體化使中國的農業遭遇了極大的衝擊,與農業血脈相連的農村佛教,自是雪上加霜。寺內勞力不足,耕種僱人又不合算,除少量的茶園與菜田外,龜山寺的田園已拋荒多年。雜草瘋長蔓延,正在合圍寺院。
後現代社會價值取向的平民化,市場經濟時代意識觀念的物質化,也使得本有濃厚避世色彩的佛教,更趨邊緣化了。盤山的水泥公路在改變山寺的交通格局的同時,也在改變它的生活格局。大大小小的機動車輛,運輸著形、色、聲、氣、味、名、利等新的因緣衝擊著古老的山門。
宗教的競爭也使信徒出現分流,基督教有規律的禮拜與有組織的傳教便吸引了眾多的信客。
而這深藏山中的古剎,如何應對新的形勢呢?
1999年,特大洪水在樹高林密的龜峰上撕開了兩條水路,直衝古剎,破牆入寺。大水在佛殿中嘩嘩流響,放生池裡的金魚也都被衝出了山寺。全寺僧俗在風雨中的無奈之狀,老寺工記憶猶新。我問,那菩薩呢?寺工說,菩薩也是捧大的,不捧,他能大?
住山的數天里,能容納百人同卧的客堂僅我與同事住著。即是我們,上山前也不能確定山寺是否提供住宿服務。負責客堂的寺工說,他曾提議在山下的省道出口處立一招牌,上書「千年古剎龜山寺由此進」。但當家說,不必。入寺頭一天,就見到寺工吵架,聲震殿宇,而寺僧無言。年老的副當家照顧著自己的小賣部,其他寺僧做著自己的功課,寺中事務多由寺工代管。寺工吵架中提到,寺內應是「僧管俗」,怎麼成了「俗管僧」了呢?
逃至深山的僧人,企圖避開塵世紛擾,遠離社會矛盾。環境決定意識,環境的簡樸固然能造成意識的純凈。但佛之慈悲在於普渡眾生,塵世尚且說「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菩薩食人間香火,難道可以享用免費午餐而無需回報人間?
流水淙淙,匯聚水庫後壓入山下的千家萬戶,水聲中有沒有古剎的隱隱鍾音?白雲團團,掠過龜山後又遮蔭塵世,雲團里,有沒有山寺的裊裊青煙?流水淙淙地去了,流雲緩緩地去了,寺僧默默地去了——去往何處呢?



推薦閱讀:
※了解一些「絲綢之路」知識吧,會讓你的「西北之行」更有深度!
※深度三國:心存漢室之急火攻心
※《幸福秘籍》好夫妻,靠的是互補互愛!深度好文!果斷收藏!
※被高估的顏值【深度好文/127期】
※悟(深度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