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史記》文章為什麼精彩
宮崎市定:馮道與汪兆銘
《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上中下三冊,實在太好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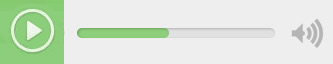
在這一篇小文中,我希望實現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對《史記》行文的探討,為《史記》的成書提供一個新的觀點。但這樣的想法在旁人看來也許過於古怪,所以我想稍微繞點遠路,先談談自己平時的一些想法,若能得到讀者的贊同,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但如果讀者看到一半就合上書本,棄之一旁,那麼我的企圖也就徹底失敗了。
一
毋庸置疑,肢體的動作和語言都是人們傳達意志的手段,但語言最終會以文字的形式形成文章,甚至進化為藝術的一種———文學。中國文學的顯著特徵之一就是,在漢字固有性質的基礎上,容易形成用眼睛來讀的文章,其表現方法有著很強的固化傾向。所謂的「古文」和「擬古文」,雖然已經不再實用,但卻一直保持著作為文章正道的權威。這些文章中所描寫的肢體動作,不知何時就被固化,甚至概念化。例如形容憤怒地從座位上站起來的時候,就經常會套用「拂袖而起」這個詞,甚至有不少人在翻譯西洋文學的時候都在套用。仔細想想,西服的袖子很窄,根本就無法拂袖,於是落下了笑柄。
但是,在肢體動作的表現方法被固化之前,應該有過一個生動寫實的時代。即使在被固化的同時,肢體動作也在維持著自己領域,將自身的價值提升為一種值得欣賞的演技,這就是舞蹈。還有一種是與語言結合所形成的動態藝術,這就是戲曲。尚未達到戲曲水平的說唱、說書、相聲等,也和我國的「講談」、「落語」,無疑加入了很多肢體動作的成分。如果將戲曲和說唱等也歸入文學的話,那麼,肢體動作還依然存在於文學當中,只是不斷地在疏離主流的同時,還時常主張自己獨特的存在價值。
成書於明代的《水滸傳》,是中國文學中首屈一指的傑作。已經有很多人指出,它是在宋元以來發展起來的戲曲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水滸傳》,其中有些部分是取自在舞台上表演的戲曲。比如一百回本的第七十三回「梁山泊雙獻頭」,無疑就是取材於《元曲選》壬集康進之的《李逵負荊》。
在這種情況下,原文的面貌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保留,這取決於素材的價值與可用性,以及《水滸傳》作者當時的心境和文筆了,因此很難一概而論。我在通讀了《水滸傳》後發現,將戲曲成分最完整地加以保留並使之成為《水滸傳》一部分的,要數一百回本的第五十三回《李逵斧劈羅真人》。
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在《水滸傳》里,李逵這個人物的基調是一個悲劇性的英雄,但雜劇中的李逵,則屢屢扮演純真的搞笑者或喜劇中的丑角。而把喜劇性的純真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正是《斧劈羅真人》中的李逵。李逵在神行太保戴宗的陪同下一同使用神行術前往二仙山迎請公孫勝的一段,讀後著實讓人捧腹大笑。這一段使觀眾開懷大笑的舞台表演中,加入了豐富的肢體動作,全然不見此前與浪里白條張順進行水陸大戰時的那般豪傑風采。讓我們一起來讀一讀《水滸傳》中的這段原文。
戴宗取四個甲馬,去李逵兩隻腿上也縛了,分付道:「你前面酒食店裡等我。」戴宗念念有詞,吹口氣在李逵腿上,李逵拽開腳步,渾如駕雲的一般,飛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著他忍一日餓。」戴宗也自拴上甲馬,隨後趕來。李逵不省得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只聽耳朵邊風雨之聲,兩邊房屋樹木,一似連排價倒了的,腳底下如雲催霧趲。李逵怕將起來,幾遍待要住腳,兩條腿那裡收拾得住,卻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腳不點地,只管的走去了。看見酒肉飯店,又不能夠入去買吃,李逵只得叫:「爺爺,且住一住!」看看走到紅日平西,肚裡又飢又渴,越不能夠住腳,驚得一身臭汗,氣喘作一團。
戴宗從背後趕來,叫道:「李大哥,怎的不買些點心吃了去?」
李逵應道:「哥哥,救我一救,餓殺鐵牛也!」
戴宗懷裡摸出幾個炊餅來自吃。
李逵叫道:「我不能夠住腳買吃,你與我兩個充饑。」
戴宗道:「兄弟,你走上來與你吃。」李逵伸著手,只隔一丈來遠近,只接不著。
李逵叫道:「好哥哥,等我一等。」
戴宗一本正經道:「便是今日有些蹺蹊,我的兩條腿也不能夠住。」
李逵道:「阿也!我的這鳥腳不由我半分,自這般走了去,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來。」
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
李逵道:「好哥哥,休使道兒耍我,砍了腿下來,你卻笑我。」
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 今日連我也走不得住,你自走去。」
李逵叫道:「好爺爺,你饒我住一住!」
戴宗道:「我的這法,不許吃葷,第一戒的是牛肉。若還吃了一塊牛肉,直要走十萬里,方才得住。」
李逵道:「卻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瞞著哥哥,真箇偷買幾斤牛肉吃了,正是怎麼好!」
戴宗忍笑道:「怪得今日連我的這腿也收不住,只用去天盡頭走一遭了,慢慢地卻得三五年,方才回得來。」
李逵聽罷,叫起撞天屈來。
戴宗笑道:「你從今已後,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罷得這法。」
李逵道:「老爹,我今都依你便了。」
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瞞著我吃葷么?」
李逵道:「今後但吃葷,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我見哥哥要吃素,鐵牛卻吃不得,因此上瞞著哥哥,今後並不敢了。」
戴宗道:「既是恁地,饒你這一遍!」退後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聲:「住!」李逵卻似釘住了的一般,兩隻腳立定地下,挪移不動。
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來。」
李逵正待抬腳,那裡移得動,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鐵鑄就了的。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晚夕怎地得去?」便叫道:「哥哥救我一救。」
戴宗轉回頭來笑道:「你今番依我說么?」
李逵道:「你是我親爺,卻是不敢違了你的言語。」
戴宗道:「你今番卻要依我。」便把手綰了李逵,喝聲:「起!」兩個輕輕地走了去。
以上文字是我依據平岡龍城的《標註訓譯水滸傳》試著翻譯的。這一段文字中的肢體動作表現得非常詳細,讀者甚至可以想像得到比這更滑稽的場景,帶點的部分【編按:標紅處理】是翻譯成日語時為便於理解而添加的詞句。此外,李逵著急時的神情和為難的動作,一字不提反而更好。
在這一段引文之後還有李逵被羅真人用法術懸在空中,以及在薊州入獄時頭上被澆了糞水的場景,讀了文字以後,讀者的眼前完全可以浮現出李逵那滑稽至極的肢體動作。
《水滸傳》的這部分內容到底是根據哪一部戲曲或者哪出評話來的,可惜已經無法知曉。但通過品味這段文字即可知道,原作無疑是一出著眼於用滑稽動作來感染觀眾的演藝。
在正統的古文之外,宋代出現了把肢體動作和語言緊密相連的表演,最終發展了一種藝術,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社會中,以都市為中心出現了一批有閑階級。他們不一定都是富裕階層,可以是不當差的軍人,也可以是商人,甚至是普通的勞動者,只要有空閑,他們就會聚集在被稱為「瓦肆」的娛樂場所來打發時間。但這樣的社會狀況在中國並不是到了宋代才出現的,在遙遠的戰國到西漢初期,以當時的大都市為中心,也存在著這樣一批有閑階級,他們同樣也需要通過各種娛樂來打發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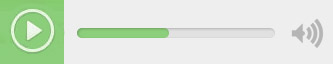
二
相似的社會狀態會產生相似的文學。像《李逵斧劈羅真人》這樣讀了文字就能讓讀者想起表演者肢體動作的文章,竟然也出現在《史記》之中,而且出奇的類似,這著實令人吃驚。當然,這樣的例子多見於《史記》的「列傳」之中,但也不只限於「列傳」。
後世的正史,帝王的「本紀」原則上是依據朝廷保存下來的實錄編纂的,而「列傳」則有時會取材於民間的野史。但在司馬遷的時代,這樣的傳統還沒有形成,帝王「本紀」的編寫,無疑是依據經典以及秦漢時期朝廷所作的記錄,但也有一部分來自民間的傳聞。如《秦始皇本紀》的一開頭說:「庄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作者顯然是把秦始皇當成了呂不韋的兒子。這樣的記錄自然不可能見於秦國的記載,即使是在漢朝建立後前朝之事已變得無關緊要的時代,這樣的記載也很難留存於朝廷的官方記錄中。《史記》的這一段話,無疑是使用了《呂不韋列傳》中的部分材料。
即便如此,《史記》的這一段文章仍然很特別。在極短的文章中,「生」這個字竟重複使用了三回。後世人若寫出這樣的文章,科舉自然是通不過的,就算是讓私塾老師修改,也會被改得滿紙皆紅。
那麼,司馬遷為什麼寫出了這樣的文章呢?或許這就是直接記錄口語的結果。同一文字的反覆,除了《詩經》中有意為之等特殊場合外,出現在司馬遷的時代,應該是相當扎眼的。但是,在聽人說話的時候,文字的反覆就不顯得那麼刺耳了。
從此也可以推斷出,《呂不韋列傳》的材料,也是司馬遷從民間的口傳中聽來的。那麼這樣的口傳,在民間究竟是怎樣口耳相傳的呢?
《史記》被譽為極善於寫實,但其中稱得上名篇的部分卻多半來自民間的口傳,依據記錄寫下來的部分反而顯得枯燥無味,如《樊噲列傳》等。而且依據口傳寫下來的部分,不僅是直接記錄了當時的口語,或許在說話的時候還明顯意識到了聽眾的存在。以《信陵君列傳》為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其中的「睥睨」二字,在張守節《史記正義》中與上文相連成句,而在《資治通鑒》胡注中則與下文相連成句。其實它既不接上,也不接下,應當是獨立的一句話。漢語中通常是四字成句,因此一句話通常是四拍,而兩個字成句的時候則需放慢語速,把一個字拖成兩個字來讀,也就是一字一頓的讀成「pī iì nī ií」,由此產生的時間差,就可以讓人感受到睥睨周圍的動作了。此後還有「微察公子」一句,也就是偷偷地觀察公子的動作。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對《淮陰侯列傳》中韓信受胯下之辱這一段的分析。屠中少年聚集在一起羞辱韓信,所謂「屠中少年」,就是混跡於肉店的不良少年,並不是店裡的夥計,若是夥計,行為如此乖張,就很難招來顧客了。《史記》是這樣寫的:「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下!』於是信孰視之,俯出袴下,蒲伏。」其中的「於是」二字,也是為了喚起讀者的注意。或許說唱人像說唱那樣,在講完少年的話後,就面朝觀眾說:「大家猜怎麼著?韓信一聲不吭地盯著對方,突然蹲下身來,從那人的褲襠底下爬了過去。」帶著這樣的心境,說唱人通過「於是」這個詞,給觀眾提供了和韓信一同思考的時間。「蒲伏」即「匍匐」,也是兩字獨立成句,說唱人也許還真的表演了蒲伏的動作。
「於是」和「蒲伏」都是兩字成句,和前面的「睥睨」一樣,一定都是拖長了音調來說的。
到了後世,作者為了盡量減少讀者的負擔,寫文章的時候,通常都會斟酌文句的長短,恰到好處地斷句,自然就形成了一種節奏。但《史記》的情況略有不同。讀者在想像當時狀況的同時,還要顧及肢體的動作,因此,必須由讀者自己承擔起調節文句長短節奏來閱讀的義務。
《史記·刺客列傳》在寫荊軻時,就出現了多次文辭的重複,而且重複的文章還很長。首先是燕太子丹與田光先生的對話:
太子逢迎(田光),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原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原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原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諾。」
田光辭別太子丹後就去見荊軻了。田光與太子丹的主要對話,也就是上文中加點的地方,在與荊軻講話時,大部分都作了重複:
(田光)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原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原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原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
用後世的語法來看,這樣的寫法非常啰嗦。但《史記》的文章不單是作文,重複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這一段都是在講故事,說唱人要加入肢體動作,時而扮演太子丹,時而扮演田光先生,時而又要扮演荊軻,司馬遷把說唱人在觀眾面前所說的話就此記錄了下來。田光先生與荊軻的對話中,前半部分,如果是後世人寫文章,一定會被省略,因為省略後也不會影響理解。但是,此處正是講故事的關鍵所在。壯士之間以命相托,是一場電光火石般的交涉場面。說唱人時而扮演田光先生,時而扮演荊軻,一瞬間似乎連觀眾的存在都忘記了。田光先生的一番話,必須要說動在場的荊軻,這時如果省略了他事前與太子丹的對話,故事的光彩就減少了一大半。
在日本最寫實的單口相聲中,很多情況下都會不厭其煩地重複很多遍,如果是比較抒情的評話,則可以適當省略。《史記》中此後荊軻見燕太子丹時,「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再次重複了田光的話。因為是帶有肢體動作的說唱,因此,在描寫情況緊迫的時候也必然會帶有喊叫聲。《刺客列傳》中荊軻刺秦王的場面就是如此:
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葯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
在這一段描寫中,「時(卒)惶急」三字似乎出現了三次,就像相撲時裁判大喊「穩住,穩住」一樣,如果換作奧運比賽,那就是「加油」了。如果要把這一段的語氣翻譯出來的話,這就是:
地圖展開後就露出了一把匕首。荊軻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起匕首向秦王刺去,但卻怎麼也夠不著。秦王大驚,掙脫著站起身來,袖子被扯了下來。秦王想拔劍,可劍太長,只握住了劍鞘。啊,危險,危險,危險啊!劍鞘太硬,一時又拔不出劍來。荊軻追趕秦王,秦王只好繞著柱子跑。群臣一個個都驚嚇得合不上嘴,因事出突然,大家都不知所措。更糟糕的是,秦國的法律規定群臣上殿不得攜帶任何利器,手持武器的警衛們都列隊站在殿外階下,沒有詔命不得上殿。事出緊急,沒時間召集殿外的士兵。於是荊軻在殿內不停地追趕著秦王。快追到了,荊軻,加油!眾人想反擊,卻苦於手中沒有武器,還有人想空手制服荊軻。就在此時,侍醫夏無且將手中的葯袋投向了荊軻。秦王還在繞著柱子奔跑。快追到了,還差一點!但荊軻始終未能得手。左右的人終於意識到了,大喊:「大王,用劍!用劍!」秦王終於把劍拔了出來,刺向了荊軻,一劍砍斷了荊軻的左腿,荊軻一下子跌倒在地。
如果聽眾們知道故事的梗概,當說唱人講到「卒惶急」的地方,就會一同拍手打起節拍來,這樣的場面一定非常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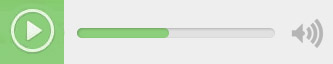
三
《史記》中最富戲劇性的場面,就要數《項羽本紀》中著名的鴻門宴一節了,這一段從頭到尾都明顯地保留著說唱的痕迹。首先,說唱人通過項王、項伯、范增、沛公和張良這五個重要人物就座的位次來展現舞台。
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
如果只是為了閱讀,這樣的文章就顯得太啰嗦了。即使是把《信陵君列傳》中的「睥睨」二字和《淮陰侯列傳》中的「於是」二字原封不動地寫進《資治通鑒》中去的司馬光,在敘述鴻門宴時,也同《漢書》一樣將之省略了,因為省略這些描寫並不影響對故事的理解。從文章來說這不是一段好文章,但如果站在說唱人的立場上呢,意境就完全不一樣了。「項王的右手邊是項伯,兩人都朝東坐了下來。亞父面朝南坐,噢,這亞父就是范曾。沛公面朝北坐了下來後,張良馬上過來,面西坐了下來時刻準備侍奉」。這是說唱人一邊講解一邊表演場景,這樣一來,文中的重複就一點也不枯燥了。
這裡需要注意一下的是他們的坐法。眾所周知,直到漢代,中國人都和現在的日本人一樣直接正坐在墊席上,當時軍中也可能會坐在什麼東西上了,但從接下來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鴻門宴上各人的坐法還是和日本一樣的正坐。因為當樊噲闖入軍帳時,大吃一驚的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跽和普通的跪一樣,在日語中都訓讀為「ひざまずく」,因為同是膝蓋著地,所以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有了相同的讀音,很容易產生誤解。「跽」是膝蓋著地,腰板挺直的樣子,從高的姿勢變為跽,就等同於跪,而從低的姿勢變成跽,就好像要站起來一樣。「項王大吃一驚,一手握住劍柄,直起身來,大喝道:『來者何人?』」這樣一翻譯就更好理解了。
無論如何,說唱人每次說到坐的時候肯定都要表演出威儀堂堂坐下來的樣子,如此重複就能顯示出動作的莊嚴感。同時,這樣的舞台設計也為接下來的項莊入謁和樊噲闖入埋下了伏筆。
鴻門宴座位示意圖
這一段描述中四句相似的句子突然被一句「亞父者范增也」打破了,但這並不僅僅是修辭,而是在實際表演中接下來的起身留下必要的時間空白。如圖所示,從表演項王落座到表演亞父落座,需要的時間很短,可是,從亞父的座位到沛公的座位就得多走幾步,在這一段空白的時間內,說唱人正好可以用一句「亞父指的就是范曾」來填補。如果這一句單是為了說明範增作為亞父的身份,那麼完全可以放在其他更合適的地方。其實,在《漢書·高祖本紀》中,鴻門宴的座次是被省略的,所以對亞父身份的說明,早在之前范增勸項羽殺沛公的地方就已經交代了;而《資治通鑒》則在後面獻給范增玉斗一隻的地方作了交代。《漢書》交代范增身份的地方應該是最恰當的。
接著,亞父授意項莊進來祝壽,意在假裝舞劍刺殺沛公,項伯見狀也起身舞劍,意在保護沛公。《史記》所言「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兩句緊挨,讓人能感受到事態的緊迫,因此自古以來就被稱讚為絕妙之辭。其實,說唱人必須一人分飾兩個角色,在如此緊迫的場合下根本就沒有時間插進「見事緊急」、「察其意」這樣的說明文字。
為了進一步提高表演的效果,說唱人還必須埋好伏筆。光靠賣力的表演來吸引觀眾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最後讓觀眾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評書的言辭通常是勸善懲惡,或宣揚因果報應,就像單口相聲最後要有個結尾一樣。如此想來,《史記》中源自說唱的故事中,很多都隱藏著一種伏筆。
《信陵君列傳》中信陵君不得已殺了魏將晉鄙,率領魏軍前來救趙,最後敵國秦國卻通過晉鄙的門客進行反間,把信陵君拉下了台。《留侯世家》中,張良在下邳的橋上邂逅老人,得到了兵書,後來果然如老人所言在谷城山下找到了黃石,並給予了隆重的祭拜,由此作為故事的結局。尤其風趣的是《陳涉世家》,陳涉年輕時曾與他人一起幫人耕地,「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單是這麼一段就非常有趣了。此後陳涉起兵反秦,雖然在陳王之位上坐得不久,但也已經能給全文畫上圓滿的句號了。可故事卻安排了另一個結局,那就是他當上陳王后正躊躇滿志的時候,此前一起幫人耕地的朋友出現在他的面前。「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官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 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作為洞穿人情的故事,比起先前的大話,這樣的故事才更有趣。燕雀終究還是燕雀,騰達之人最討厭別人把自己貧寒時的事拿出來說事,最後這個人果然觸怒了陳涉而丟了性命。在敘述一個平庸傻瓜的命運的同時,也昭示了陳涉亦非鴻鵠,陳涉缺少容納愚蠢故人的度量,也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
不過,《史記》中有的故事也有兩個以上的伏筆,《刺客列傳》中荊軻的故事便是如此。
在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中,燕太子丹和秦王政少年時同在趙國做質子,當時兩人非常友善。但當秦王政當上國王后,太子丹作為質子去秦國卻遭到了冷遇,於是,他一氣之下逃回燕國並展開了復仇的計劃。故事從這裡開始,到暗殺失敗、燕國滅亡為止,歷史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起始和結尾。然而,故事的開始總是讓人覺得很不自然。秦始皇是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生於趙國都城邯鄲的,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昭襄王去世,孝文王繼位後馬上就被送回了秦國。也就是說,生於趙國的秦始皇,在趙國只呆了九年,頂多就是十歲。即使其間與燕太子丹友善,那也只不過是玩伴而已,太子丹以此為由,在入秦為質時認為秦王政冷遇了自己,這樣的想法本身就沒有道理,也沒有理由被載入史冊。這麼做,不如說只是為故事提供一個有趣的開端而已。而且對說唱人來說,比起天下大勢,以個人間的情感糾葛為切入口,那才會更加引人入勝。
荊軻只帶了一個隨從就潛入了如日中天的秦國,還在眾目睽睽下刺殺秦王,這故事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議。為了使聽眾能夠接受這個故事,就必須先介紹燕國的遊俠風氣,使聽眾感受到一旦情投意合便可兩肋插刀的氛圍。由此出場的就是田光先生和高漸離。荊軻和高漸離的關係就是第二重伏筆,從兩人游於燕市,高漸離擊築、荊軻唱歌開始,以最後高漸離刺殺秦王的失敗作結。其實故事中還存在著第三層伏筆,那就是荊軻和魯句踐的關係。荊軻曾因賭博和魯句踐爭吵,被魯句踐教訓後逃之夭夭,這個故事為荊軻對自己的武藝缺乏信心,想等武藝高超的同伴來後一起前往秦國埋下了伏筆。但在太子丹的催促下,荊軻不得已與燕國勇士秦舞陽一起出發了,但這個秦舞陽在此後的刺秦中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這段故事最後以魯句踐的「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荊軻的故事,不僅敘事宏大,而且結構嚴整,尤其是第三個布局,兼備起承轉合之妙,可謂無懈可擊。但若是將之當成史實,那麼這樣的故事就顯得有趣過頭了。作為史實,或許最初就只有燕太子丹與荊軻的對話,但後來加進了荊軻的友人高漸離刺殺秦王的故事,最後又加進了魯句踐的評論。
《史記·遊俠列傳》中荊軻的故事,大部分行文都與《戰國策·燕策》一致,司馬遷自己也曾說過《史記》的很多取材源自《戰國策》,所以自古以來荊軻的故事也被認為是其中一例。而方苞卻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其在《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讀子史·書刺客傳後》中說:「余少讀燕策荊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之舊文決矣。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口道,則決非《國策》舊文。」對於方苞的說法,我還不能就此贊同,畢竟司馬遷在《刺客列傳》的贊語中寫道: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夏無且就是在荊軻刺秦王時向荊軻投擲葯囊的御醫,方苞因此認為荊軻的故事都出自夏無且,然後經公孫季功和董生之口傳到了司馬遷的耳中,事實恐非如此。夏無且能傳達的,不過是荊軻沒能傷及秦王以及自己因功受賞之事。司馬遷關於荊軻的故事,更多的是來自「世言」,亦即世間的傳聞,但他並不是不加區別地採用,而是對各種傳說進行判斷,排除了過於神怪以及非常明顯的反證,而夏無且的話也不過是反證之一罷了。
儘管如此,我卻不反對方苞的結論,亦即《戰國策》取文於《史記》,這是因為還有些其他原因。《燕策》的敘事中沒有充分的伏筆,給人一種故事情節不完整的感覺。也就是說,《燕策》中首尾沒有魯句踐的故事,中間卻又有與之相關的秦舞陽的故事;沒有荊軻與高漸離游於燕市的故事,中間卻又有高漸離在易水擊築,以及最後刺殺秦王未遂等故事。這些都給人一種支離破碎的感覺。
那麼,為什麼《戰國策》要重新從《史記》中引入文字呢?這或許是因為《戰國策》中本來就有荊軻的故事,而且是從燕太子丹怨秦開始的,加上文章拙劣,與《史記》相比不免遜色。於是就有好事者從《史記·遊俠列傳》的荊軻故事中截取文字加以取代,但對荊軻與魯句踐發生口角,以及荊軻與高漸離游於燕市的情節卻棄之不顧,因此導致了《戰國策》的行文前後缺乏呼應的結果。
《史記》中對生動場面進行描寫時,比如在鴻門宴這一段中,司馬遷採用了「語」這樣一個表述方法。《史記·留侯世家》全部省略了這一段,僅用「語在《項羽》事中」一句了結。同樣是《留侯世家》,漢王劉邦接受張良的建議,授予韓信齊王印綬,以及依張良之計賜各諸侯土地並向其徵兵,這些內容也都省略了,分別以「語在《淮陰》事中」和「語在《項籍》事中」進行了交代。另外,司馬遷還用了「雜語」這個辭彙。《太史公自序》最後提到「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史記正義》將此處讀為「六經的異傳,百家的雜語」,但方苞將其解讀為「六經和異傳」。方苞在《抗希堂十六種·史記注補正》中進行了解釋:「言合六經並別傳之書,以為史記也。」把「異傳」解釋為「別傳」,並將之作為與六經並存的素材。真是如此,則下面的「百家雜語」也必須理解成「百家之說和雜語」,這樣的解釋應當是合理的。
那麼,這些被稱為「語」或「雜語」的故事又是哪些人在傳頌呢?中國的史學家大多基於《周禮》的思考模式,認為所有的文化都是由朝廷的官員掌握的,我非常不贊成這樣死板的思維方式。
司馬遷屢屢使用「長老」一詞,長老所言,是其編寫《史記》時的素材來源之一。《黃帝本紀》「太史公曰」中寫道:「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其中的「學者」或儒者,相當於前面所講的「六經」,「所傳」無外乎「異傳」,而所謂的「長老」,就是不同於「百家」的民間故事,也就相當於前文中出現的「雜語」。《史記》對取材的說明,從首篇《五帝本紀》的說明到終篇《太史公自序》,首尾均可對應得起來。
《史記》中引用民間諺語時也常常使用「語」這個字,尤其是散見於「論贊」之中。例如《管晏列傳》稱:「語曰:順將其美,匡救其惡。」《孫子吳起列傳》中稱:「語曰:能行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行。」將其作為諺語應用的,如《李將軍列傳》中「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佞幸列傳》中「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故無虛言」。同樣,在引用鄙語時亦有說明,《白起王翦列傳》中「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平原君虞卿列傳》中「鄙語曰:利令智昏」,等等。
那麼,先前所說的「雜語」與這裡的「鄙語」之間又有著怎樣的共同點呢?首先它們都是自古流傳下來的熟語。與「鄙語曰」相同的情況下,有的地方用了「古人有言」,如《三王世家》中「古人有言: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如前所說,「雜語」是所謂長老流傳下來的智慧,長老則是熟知各種口頭傳說的百事通。《龜策列傳》太史公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雲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因此,「雜語」可以說是當時的智慧寶庫。
那麼,這樣的說唱又在哪裡表演呢?類似的演出,在王侯的宮廷中通常由倡優來表演,私塾老師在向弟子講述故事時也無疑也會帶有表演的成分。但所謂的「雜語」並非源於倡優或學者,而是來自普通市民中通曉百事的長老,所以場地應該就是都市裡的「市」。古代的市不僅是經商之處,也是市民休憩的地方,更是有閑階級打發時間的娛樂場所。雖說是娛樂場所,但也不可能有劇場、電影院、音樂廳那樣的設施,只不過是市民聚在一起相互攀談、相互聆聽、相互表演取樂而已。好在古人不像近代人這樣喜新厭舊,同一個故事無論聽多少遍都不會覺得厭倦。故事的原型是基本固定的,但經過反覆表演,其中的內容就變得洗鍊起來。對文學而言,民眾才是偉大的創造者、理解者、批評者,是人民的寬容,才促成了文學的不斷成長。只是在這個過程中,也會為便於講述,對故事的細節進行加工和改造。
司馬遷對其搜集和篩選的民間故事進行加工,將其寫入了《史記》。如同很多史家一樣,他不是創作者,只是編纂者。不過他在取捨素材時的慧眼,是別的史家望塵莫及的。同時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也有一些史實以外的、完全由說唱人編造的東西,騙過了他的雙眼,混入了《史記》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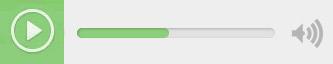
四
為了明確《史記》作為歷史著作的特徵及其文章的特點,有必要將其與《漢書》進行一次比較。特徵也好,特點也好,總之都是相對而言的。從司馬遷的《史記》到班固的《漢書》,不單是從通史到斷代史這一形式上的變化,還關係到更加本質的變化。如果先說結論的話,這就是:從文章上來看,《漢書》不如說是退步了,但從歷史著作這個角度來看,則《漢書》確實取得了進步。凡事總有利弊,這個問題也必須同時考慮到內外兩面的因素。
《史記》的文章,由於司馬遷努力汲取民間的說唱故事,因而顯得非常寫實,也非常精彩,人物個性栩栩如生。但若要將之作為嚴格的史料,那麼有時就不得不好好思考一下它的可信度了。當然,司馬遷並非不加分辨地採用民間傳聞,而是經過了自己的取捨,這從上文談到的《刺客列傳》中就可以看出。《蘇秦列傳》的贊語中也說:「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可見世間有很多附會在蘇秦身上的逸事,司馬遷只從「世言」中選出了他認為可信的資料,將之寫進了蘇秦的傳記。儘管如此,《蘇秦傳》中在談到合縱成功時說:「秦兵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對這句話,自古以來就不乏用詞過甚的批評。
平心而論,《史記》的文章越是美妙之處,從史實的角度來看就越容易成為其弱點,甚至是一處硬傷。鴻門宴中項羽究竟是不是面東而坐,這個問題,從絕對史實角度來看,即便是普通的史家,他們與生俱來的猜疑心都會難以容忍。我們所能確信的只有一點,這就是司馬遷確實聽到過這樣的故事。
《漢書》多處採用了《史記》的記載,但其中也有班固自己的取捨。班固的文章非常厭惡敘述的重複,因此,敘述鴻門宴時絕不會言及項羽和沛公的座次。不僅不會言及座次,《漢書·高祖本紀》雖取材於《史記·項羽本紀》,但他竟冷酷到不顧這樣的改寫會使文章黯然失色,只是將項羽、項伯、范增、沛公、張良和樊噲的行動保留了一個輪廓而已。於是我們在《張良傳》中看到的是「語在《羽傳》」,在《項羽傳》中又是「語在《高紀》」,因此,《高祖本紀》才是其最根本的部分。《樊噲傳》中只保留了他言行的輪廓,所佔篇幅只有《史記·項羽本紀》相關部分的大約三分之一。文章變得無趣的確是事實,然而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卻是除去了贅肉,得以把史實壓縮到可信賴的範圍之中。因此從歷史學的立場上來看,《班固》的做法確實是一種進步。
但要說班固是否完全貫徹了他的史學思想,那倒也不一定,也有不徹底的地方。他在《張良傳》張良遇見黃石公的那一段,以及《陳勝傳》中當初的佣耕者前來做客的那一段,完全繼承了《史記》的文字。張良與黃石公約定見面時間卻遲到的情節,其實沒有也無妨,即便有的話,一次也就夠了。對於說唱人來說必要的重複,但對讀者來說只是多餘的重複。還有,來陳勝處做客的佣耕者用了楚方言「夥」這一段,原本的著眼點在於說唱時的效果,如果單作為用來閱讀的文章,那就顯得沒有什麼生趣了。班固如果忠實於自己的信念,此處就應該改得比《史記》更簡潔、更無聊,這樣作為科學性的歷史才顯得更可信。
史實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寫得生趣,歷史的真實與文學的真實能否一致?不僅是漢代,我們今天依舊為此而煩惱。
司馬遷的時代,通過文字記錄下來的史料還很少,因此,他要書寫漢以前的悠久歷史,就勢必從民間的口傳中發掘材料。所有的口傳都有地域性,各地流傳的話題都不相同,因此他經常外出旅行,在當地聽取民間的口傳,走訪口傳中提及的遺迹。《史記·信陵君列傳》中說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之後,又借侯嬴之口說出「嬴乃夷門抱關者」。此外的夷門多次在故事中出現,可見司馬遷確實對夷門進行過實地考察,確定過夷門的存在。在《信陵君列傳》的贊語中,「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這段話讓我們感受到司馬遷看到了夷門,於是確信信陵君的事實不誤後的那種如釋重負的神情。此外,他還走訪了韓母墓,尋訪了豐沛蕭、曹、樊噲等人的故居。
然而,到了班固的時代,文字記錄的史料急劇增加,尤其是身為宮廷史家的班固,能夠自由地閱讀內府所藏的史料,加上書寫的對象僅限於漢代,因此他的工作就完全成了書齋里的工程,也就是書桌上的歷史學了。司馬遷雖然從父輩起就是宮廷史家,但他仍保留著庶民的一面。雖然把儒家作為學問的正統,但卻沒有因此而排斥百家。而班固同樣是宮廷史家,比起市民的自覺來,更多的則是作為貴族的自覺,加上當時已經形成了獨尊儒術的形勢,闡明儒學的真意才是學者的任務,因此班固對司馬遷不遺餘力尋訪的市井史料嗤之以鼻,稱為「小說家」之言。《漢書·藝文志》「小說家」條中就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志。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也就是說,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小說,是閭里的小民所作,君子不應積极參与。雖不全面排斥,其實不值一文。公平而言,《史記》中多處採用了這樣的街談巷語,而班固對《史記》又多有採錄,其實不知不覺就間接且大規模地採用了街談巷語。把古代的傳聞當作史實加以珍視,又將當代流行的巷語一概斥為荒唐,這是歷史學家經常容易犯的錯誤,班固也在所難免。
司馬遷的時代還沒有形成後世那樣的學問分類,但在儒學體系中,把儒家經典奉為不容置疑的真理,其他知識則是「傳」,起到輔佐經典的作用。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儒家經典中自然包含了屬於歷史學的《尚書》和《春秋》。當時不僅經、史未分,同時子、史也還沒有分離,《荀子》、《國語》、《左傳》都是被視為「傳」的。在那樣的時代,司馬遷成就了一家之言,但在後世經、史分離後,司馬遷被尊奉為史學的鼻祖,這恐怕他自己做夢都沒有想到。
司馬遷要敘述的時代,既包括《尚書》、《春秋》等古典已經敘述了的古代,也包括此後的整個百家爭鳴的時代。秦代的《呂氏春秋》,以十二紀、八覽、六論的分類方法,試圖將當時所有的知識進行網羅。司馬遷的設想其實與《呂氏春秋》非常接近,也是以時代和地域為經緯,撰成了可稱得上是百科全書的《史記》。司馬遷撰寫《史記》,並不像後人所想像的那樣要撰述一部歷史著作,他只是在撰述這些人和事的時候採用了歷史著作的形式。在這裡,司馬遷對自己認為值得傳至後世的東西進行了忠實的記錄,民間的口碑之所以要保存,不僅是因為作為其核心內容的史實值得保存,也是因為說唱這種形式本身就具有保存的價值。雅俗未分,是《史記》的顯著特徵之一。
雖然班固的《漢書》繼承了司馬遷《史記》的體裁,但兩者在敘事意圖上有著很大的差異。一般把《史記》稱為通史,把《漢書》稱為斷代史,這不單是敘事時間上的長短,應該還有著其他含義。作為斷代史,《漢書》與後代正史中的其他斷代史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班固是東漢人,雖說是東漢,但終究和西漢是同一個王室,所以班固寫的其實是當代史。後世的正史都是把前朝的歷史當作過去的事來編纂,而《漢書》卻是把西漢的歷史當作當代史在書寫。所以對班固來說,《漢書》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一部歷史著作,更在於它是漢代的歷史。在漢代人看來,漢王朝比此前的任何時代都要光芒四射,有著至高的權威。而且漢王朝把儒學定為國教,用儒學思想來指導國民是其基本國策,因此,光大這一國策就是班固最大的責任。因此,班固撰述的歷史,是衣冠楚楚、一本正經的士人君子式的歷史,是所謂的街談巷語無法企及的典雅文章。
然而,《漢書》對《史記》體裁的繼承,給後世帶來了巨大影響,從此規定了歷史記述的方向,這好比是兩個點就能決定一條直線一樣。於是,後世繼承《漢書》紀傳體的史書不斷湧現,但這些現在被稱為正史的史書,無一不是對前朝歷史的敘述,根本不可能有班固撰寫《漢書》時的那般書寫現代史的感激之情,充其量不過是事務性的記錄而已。
一般認為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是為了試圖恢復通史的傳統,但《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其意義截然不同。《資治通鑒》雖是通史,但也只是貫通了幾個王朝,據說春秋之前的歷史被有意地迴避了,開篇即從戰國開始。因此,《資治通鑒》並不是包含全部歷史時期的通史,只是斷代史的集合而已。其次,雖說《資治通鑒》的文章受到了當時古文運動的影響,擺脫四六駢儷文的束縛,努力回歸漢代的傳統,成為復古主義的一翼,但司馬光所能回歸的不過是《漢書》的文章,根本無法回歸到《史記》。這一點不僅司馬光做不到,恐怕司馬光以外的所有史家也都無法實現。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司馬遷的這種精神卻在《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通俗文學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歸。
近世的古文家其實也已感受到了《史記》行文的妙處,這從《史記評林》這類書一再增補重版以及廣受歡迎的現象中就即可窺見一二。但他們只是在欣賞《史記》的文字,卻沒有想過要去模仿。恐怕也根本無法模仿,因為他們並不知道《史記》的文章到底是因為什麼才具有如此的魅力。儘管我對此也不十分瞭然,但至少通過這篇文章做了努力的探究。只是我說的這些都甚為通俗,或許會被博雅君子嘲笑為「評林本」。但是,如果要我說一句什麼話的話,那麼,我希望各位偶爾也把「評林本」之類的書籍拿來用作研究的輔助手段吧。
(本文原題《肢體動作與文學——試論<史記>的成書》,選自《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推薦閱讀:
※史記47
※史記 致寧澤濤太太們 要愛持久愛
※《史記系列講座》第二講:項羽本紀(本周末)
※史記卷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史記 八書 天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