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布盧默|莫扎特的風格與影響(下)
莫扎特的風格與影響(下)
[德]弗里德里希·布盧默 著
Jacqueline 譯
莫扎特廣泛地以同時代作品為樣板的做法促使我們考慮一種可能:劃一條分界線,他作曲活動的「年青」或「成長」時期到此為止,而屬於他自己的個人風格的成熟時期從此開始。但這條線劃在哪裡呢?1773~74年的冬天,也許?如果這樣做,就可以合理地一上來就把弦樂四重奏K.173,五重奏K.174,以及第一鋼琴協奏曲K.175【現在編為第五鋼琴協奏曲——譯註】排除在外,而把諸如G小調交響曲K.183,鋼琴奏鳴曲K.279-83(189d-h)和《假扮園丁的姑娘》K.196這樣一些有個性的作品歸入他的成熟時期。但與此同時,卻會把嬉遊曲K.136-8(125a-c),四手聯彈鋼琴奏鳴曲K.381(123a),歌劇《本都之王米特里達特》K.87(74a),《阿斯卡尼奧在阿爾巴》K.111,《希庇奧內的夢》K.126和《盧喬·西拉》K.135不合理地劃入「無個性」的作品之列。顯然這條線劃得不夠好。如果劃在這裡,就會把很多根據樣板寫成的、不那麼有莫扎特個性的作品排除在外,而其中卻不乏在風格上有意味的作品。即使是歌唱劇《巴斯蒂安與巴斯蒂安娜》K.50(46b),1768年莫扎特十二歲時的作品,難道就沒有幾個極具莫扎特風格的片段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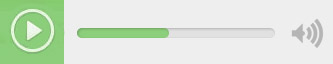
莫扎特:歌唱劇(喜歌劇)《巴斯蒂安與巴斯蒂安娜》(Bastien Und Bastienne)K.50(46b)序曲,演奏:Rinaldo Alessandrini演奏挪威國家歌劇院樂團。
把莫扎特的創作劃分為「年青」和「成熟」兩個時期的做法很容易導向荒謬。以前人們認為1777~78年冬天(曼海姆-巴黎之行)可以作為莫扎特藝術上的成熟時期開始的標誌;但是這麼劃分的人一直遭到質疑,一方面,這會把很多作品降格為「不成熟」的,而實際上不該如此;而另一方面,也絕不是巴黎之行後他寫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成熟之作。真實的莫扎特是一位普羅透斯【Proteus,希臘神話中的海老人,海神波塞冬的侍從,能預知未來,能變成各種形狀——譯註】。如果要用語言來確切地描述這位普羅透斯的風格,最好是考慮他的晚期作品,那裡莫扎特的風格特性以最精鍊的方式表現出來,卓爾不群,無懈可擊。如果藝術上的發展意味著一種不斷增長的包容力,能夠以日漸獨到的形式表達日漸精深的觀念,如果把海頓當作音樂史上這種發展的樣板,那麼毫無疑問,我們在莫扎特身上找不到任何「藝術上的發展」。年青的莫扎特就顯露出世所罕見的學習吸收才能,伴以技術掌握上驚人的早熟;而在他生命的最後有一個時期(在維也納),技術成為心智的「至上的婢女」,而歌德所謂「Fülle der Gesichte」,「幻象豐滿」【語出《浮士德》開篇《夜》——譯註】,在這些作品中被壓縮為最簡練的曲式模式。在這兩個時期之間所寫的音樂與其說是一種「發展」或持續的演進,倒不如說是那種普羅透斯本性所經歷的一場反覆的自我形變。
如果有人試圖描述莫扎特的風格,當然可以建議他從晚期作品入手;但他必須時刻注意一點:如果完全以晚期作品來確定莫扎特的個人風格,而把其他作品排除在外,將會對作曲家的個性作出完全錯誤的理解。
這一連串的思考再次把我們帶回了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的比較,展現出三大師之間的基本差異。海頓的發展前後一致,並在最後時期形成了一種風格,這種風格既是普遍適用的,又是高度個人的。從海頓晚期的交響曲回望他早期的交響曲與四重奏,看不到歧途,看不到突然的中斷,也看不到轉折。貝多芬也經歷了藝術上的發展,但這種發展絕非前後一致。它是在經過諸多歧途斷路之後,才達到了屬於一位幽居獨處者的晚期風格,而這種風格是極度個人的,絕無普遍適用的可能。從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與鋼琴奏鳴曲回望,會把這兩種體裁的早先作品視為間斷的火山噴發或偶爾的流星閃耀,從中幾乎望不見任何通向晚期作品的道路。即使在這個意義上,莫扎特也並未經歷任何個人的「發展」,他最後的每一部交響曲,每一首弦樂四重奏,每一首弦樂五重奏,都印證了他內心至深處那個自我的表現,純粹而極致。年青時代不計其數的對他人樣板的學習吸收如今熔於一爐,從中逐漸剔除了一切不相稱和無個性的成分。從此處回望他的早期作品,總體的印象會是一個不間斷的簡化、澄清和精鍊的過程。於是在路之終點,我們看到了這些特出的、純粹個人的作品,簡樸之極而精妙至深,坦率之極而含蓄至深。海頓晚年已經有能力通俗,實際上也真的流行於世,不可阻擋。晚期的貝多芬不可能通俗,他也並不打算如此。晚期的莫扎特也不可能通俗,但原因完全不同。唯一的例外是《魔笛》,極度精鍊凝聚的成分與通俗的成分混合在一起。阿諾爾德·謝林【Arnold Schering(1877-1941),德國音樂學家——譯註】把莫扎特的晚期作品描述成對那個世界主義時代的淋漓盡致的表現,這個評論是荒謬的:海頓的晚期作品若這樣說倒還大致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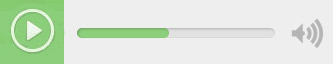
莫扎特:歌劇《唐璜》K.527選段。
莫扎特的許多作品在他去世以後即被輾轉相傳,以至流行於世,有很多複雜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當時浪漫派的詩人和作家確信自己在他的晚期作品裡發現了非現實的、他世界的、惡魔的東西,而他們正是用這些東西來建造自己的天球的。在小說《堂璜》(1814)里,E.T.A.霍夫曼說起「這全部歌劇之歌劇的深長意味」,「神和魔的角力產生了塵世的概念,正如前者的獲勝產生了天國的概念」。霍夫曼也首先意識到莫扎特在他的經典歌劇里「僅選擇確與其音樂相配的故事,雖然此類故事似乎有很多」;對霍夫曼來說,莫扎特的音樂是「遠方精靈王國的神秘語言,它那奇妙的發音在我們的內心世界迴響,喚起一種更高的、專註的生活方式」(《詩人與作曲家》,1813)。浪漫主義者轉向莫扎特,其基礎是對某些理念的深入理解,而當時認為在他的作品中能夠找到這些理念。但如果對莫扎特晚期音樂的風格缺乏深刻理解,則這一做法絕無可能;而正是風格,直觸浪漫主義一代的要害。毫無疑問,是莫扎特的旋律先於一切地打通了道路。貝多芬早期的變奏曲(1792~1801)證實了「少女還是婦人」(Ein Ma"dchen oder Weibchen"),「對男人,什麼是愛的感覺」(Bei Ma"nnern, welche Liebe fühlen),「就讓我們手挽著手」(La ci darem la mano),「你去跳舞」(Se vuol ballare)這樣一些旋律的迅速流行。許多其他旋律也很早就流傳開來。印行了《堂璜》的選段:小夜曲「你窗前的一瞥」(Deh, vieni alla finestra);采麗娜的「來,我要告訴你」(Vedrai carino);說來奇怪,還有愛爾薇拉的降E大調詠嘆調「狠心的人,你背叛了我」(Mi tradì)(填上了完全不同的德語歌詞),全都是單行版,全都在1788~89年出版。1789~90年印行了《費加羅》的選段:凱魯比諾的「你們可知道」(Voi che sapete)和伯爵-蘇姍娜的二重唱「狠心的人,為何讓我如此憔悴」(Crudel, perche finora)。《魔笛》的許多唱段早在1791年就流行開來。旋律是莫扎特音樂中最易接近的因素,在這些例子中尤為明顯,相對「簡單」的抒情旋律並未置身於高度發展的和聲布局之上。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以高度藝術化的手法精心製作一條歌體的旋律,並不能阻止它的通俗化,反而會促進它的通俗化;類似的例子有海頓的「上帝保佑弗朗茨皇帝」(Gott erhalte)(今天仍是德國的國歌);海頓的「從前,有一位矜持的女孩」(Ein Ma"dchen, das auf Ehre hielt),舒伯特的「野玫瑰」(Heidenro"slein)和「菩提樹」(Lindenbaum)。實際上,那些已經變成人們共同財富的曲調中有不少源於莫扎特技藝最為高超的旋律。突出的例子是歌曲「來吧,可愛的五月」(Komm, lieber Mai)(K.596,作於1791年),今天的每個德國學童仍然唱著它。這一旋律,如《魔笛》中的很多旋律,以一首民歌的曲調為基礎,但這一點無關緊要,因為它只有在莫扎特的版本中才變成了人們的共同財富。音樂群體里的多數人並未注意到,這種外表的簡單性實際上是反覆精鍊的結晶,這樣的旋律實際上是藝術上勤勉勞作的果實。音樂公眾摘取了果實,而後它留在公眾意識中的面貌,就成了自然流露的創意,正如歌德在談論《青年的魔角》(Des Knaben Wunderhorn)中的歌曲時所想到的:「它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使寫過,印過,現在也可以遺忘了,因為它們已經融入了這個國家的文化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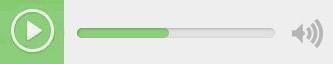
莫扎特:歌曲「來吧,可愛的五月」(Komm, lieber Mai)K.596(作於1791年),演唱: Anne Sofie von Otter,鋼琴(fortepiano):Melvyn Tan。
事實上,晚期莫扎特的旋律是卓越的藝術,外表的簡單性恰恰表明了他藝術才能上驚人的成熟性——一切對難度的暗示,一切斧鑿之痕都被消除了。里夏德·施特勞斯,他本人也是一位大旋律家,就這個問題,在1918年致信批評家馬克斯·馬沙爾克【Max Marschalk(1863-1940),德國樂評家、作曲家,R.施特勞斯與馬勒的朋友——譯註】時寫道:
「我在旋律上費時極多;從最初的樂思到最終的旋律形態要經過一條漫長的道路……動機大約是一種靈感;這就是樂思,我們當中多數人都滿足於樂思,然而真正的藝術始於樂思的展開。藝術不在於開始一條旋律,而在於它的延續,在於它向完整的旋律形態的展開……莫扎特展示了最完美的旋律形態;他的筆觸輕逸,這才是真正的目的。貝多芬的旋律稍顯沉重;明顯能感到勞作的痕迹。請你聽一下莫扎特旋律的絕妙擴展,比如凱魯比諾的『你們可知道』。你覺得它該停下來了,然而它越走越遠,越走越遠。」
施特勞斯說起他年青時勃拉姆斯如何建議他研究舒伯特舞曲的旋律結構,隨後寫道:
「旋律形態的構造當然依靠天賦;但這裡我們也涉及到了最困難的技術問題之一……看似瞬間產生的旋律幾乎總是專註勞作的結果。」
這是一段值得讚歎的描述。如果莫扎特的旋律看起來筆觸「輕逸」,這當然是他天賦的表現;但這一點只有在卓越地掌握了技術之後才成為可能。他的小姨Sophie Haibl留下一段話,描述莫扎特工作時怎樣在屋子裡踱來踱去,沉思冥想,看來證實了他在精心作出旋律之前,先要在整體協調方面付出艱苦的努力。旋律的製作是案頭工作,而創意則需要通盤的策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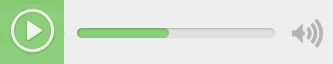
莫扎特:降B大調第27鋼琴協奏曲K.595,第二樂章 小廣板,演奏:Andreas Staier(fortepiano), Gottfried von der Goltz指揮弗萊堡巴洛克樂團。
時至今日,學生們常為莫扎特旋律中這樣的一些特性所打動,所謂「明朗」、「流暢」、「輕逸」、「完美的比例感」、「從焦躁走向平靜」。單簧管協奏曲K.622的柔板主題,鋼琴協奏曲K.595的小廣板主題,交響曲K.543的行板主題,弦樂三重奏K.563的行板主題,弦樂四重奏K.565的變奏曲主題,弦樂五重奏K.614的行板主題,單簧管五重奏K.581的小廣板主題,當然還有很多別的,它們是那些從歌劇中流行開來的旋律在器樂上的對應。它們沒有象歌劇旋律那樣流行起來,是由於它們的器樂個性:流行於大眾需要藉助歌詞。那麼這些主題的莫扎特風格確切地說是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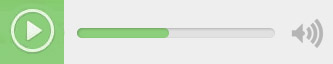
莫扎特:A大調單簧管五重奏K.581,第二樂章 小廣板,演奏:Richard Stoltzman(單簧管)、東京四重奏組。
它們都採用了簡單而基本的八小節樂段布局(雖然有許多變體)。八小節的樂段通常分成四小節的兩組,每一組通常再細分為兩小節的兩組。再不可能有更簡單的布局了。在這一Diastematic(潮起潮落)中,兩小節的細分單位形成了小的對比;這就產生了基本的布局a-b-a-b(例如,K.614的行板,K.543的行板,K.595的小廣板)。或者,第一個a後接變化的或加強的a,或許還會再接第三個a,只有第四個兩小節細分單位包含對比性的a-b(例如K.622的柔板)。有種種其他組合;它們可以輕易地背離八小節布局,而聽者幾乎不會察覺這一點;只有比例感敏銳的人才會注意到K.581的行板主題在陳述時略微延伸到九小節,而在答句中延伸到十一小節。在鋼琴協奏曲K.488的柔板中,旋律布局a-b-a-a"-a"-a延伸至十二小節之多。布局的可變性並無限制。無論旋律的格律關係如何,給人的印象總是無可挑剔的平衡感和比例感。越晚期的作品,主題越簡單,越對稱,越寧靜,越內省,越清澈。慢樂章中,或許單簧管協奏曲K.622的柔板是最完美的例子之一;鋼琴協奏曲中,最後一部K.595在全部三個樂章中所用的主題材料都是「最簡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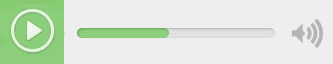
莫扎特:A大調第23鋼琴協奏曲K.488,第二樂章 柔板,演奏:Ivan Moravec、Josef Vlach指揮捷克愛樂樂團。
在莫扎特的晚期作品中,這一旋律品質總是與旋律首次呈現時的最簡單的和聲結合在一起。只用到主和弦,屬和弦與下屬和弦,以及最近關係調。通常,兩小節音組從一個基本功能移到另一個;兩小節後到達屬和弦;再過兩小節回到主和弦;六小節後或許用下屬和弦,或同名調的和弦;八小節後又是屬和弦。這個非常粗略的布局輪廓只是為了說明,從和聲的角度看,其關係也是最簡單的一種。節奏以一種略為相反的運動方式強調了主題內部的微小對比。而到了晚期的莫扎特,這種節奏上的明暗法常保留在難以察覺的細微層次上,或化為簡單的模仿(如五重奏K.614的行板),或竟完全消褪(弦樂三重奏K.563的行板)。在單簧管協奏曲K.622的柔板中,伴奏的音流幾乎持續不變,而旋律在這背景上以一種非常精巧而柔韌的節奏延伸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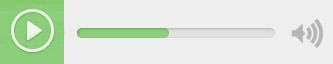
莫扎特:降E大調弦樂五重奏K.614,第二樂章 行板,演奏:Guarneri Quartet。
這樣的描述或許適用於莫扎特晚期作品中多數慢樂章的主題。不過它們同樣也適用于海頓很多慢樂章的主題,比如,Op.76,No.1的柔板,Op.76,No.2的行板,Op.76,No.5的廣板,以及Op.76,No.6的幻想曲。這些主題表明海頓不僅愛惜莫扎特,而且研究了他的作品。弦樂四重奏Op.42(1785)的行板也表露出相似的態度。還只是在不久以前,在1781年,Op.33,Nos.1,2,4,5,6的慢樂章仍然保留了一種更加裝飾化的華麗(galant)品質,旋律、節奏與和聲幾方面都處於幾無休止的、錯綜複雜的運動中;只有Op.33,No.3的行板主題非常接近莫扎特。在比較莫扎特晚期的慢樂章主題與貝多芬早期的主題時,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現象。在許多作品中,尤其是在早期的室內樂作品中,貝多芬顯然把莫扎特當成了樣板;但很快,尤其是在鋼琴奏鳴曲中,誕生了一種寬廣的、如歌的、感情飽滿的新型主題。我們遇到了一種英雄性的悲天憫人的力量,既不見於莫扎特,也不見於海頓;那種率直的、個人的言語,那種直接面對聽眾的訴求,給人以強烈的印象。而莫扎特的主題材料則把自己局限於那個飄搖著的、具有強大表現力的音樂絕對物的王國。粗略地總結一下:莫扎特的主題是超時代的,而貝多芬的主題是指明了寫給他的時代的。在最後幾年,莫扎特特徵性地「飄搖」於兩極之間——於通俗與艱深之間,於激情與雅緻之間,於感官享受與形式約束之間,若以歌德的話概括之,於「自然」與「藝術」之間——而正是這種飄搖本身,達到了它最完美最純粹的頂點。
「Natur und Kunst, sie scheinen sich zu fliehen
Und haben sich, eh" man es denkt, gefunden.」
「自然與藝術,好像在互相躲避;
不等你細想,它們又彼此找見。」
如果我們的眼光不錯,正是從這至高的頂點向下俯望,莫扎特的音樂才會進入各民族的意識,才會進入全人類的意識。
※ ※ ※
對於晚期的莫扎特,他把慢樂章的主題擴充成整個樂章的方式與這些主題本身的風格同樣重要。我們已經指出,雖然細節上有許多可變性,樂章的外部曲式總體上或多或少都遵循一個確定的布局。然而不可能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單從曲式就可以確定莫扎特的風格。從細節上看,在旋律、和聲、節奏、結構變形與變奏方面,在明暗法和音型裝飾方面,這些曲式的應用總是表現出無可比擬的豐富性,無論是海頓還是早期的貝多芬,甚至舒伯特,都不能與之相比。不僅旋律的伸展如施特勞斯所說「越走越遠,越走越遠」,而且正是從這些旋律自身生出的關聯和對比,形成了充盈的音樂現象,這些現象隨即又編織為一件緊緻的實體。從技術上看,要做到這一點,可以在主題終止之後讓新的結構作為其對立面出現,也可以讓主題自身以對位的形態變成自己的對立面。在G小調交響曲K.550的行板中,主題甚至在樂章開始的十九小節第一次出現時,就展開了三個對位動機,此後,在這一基本材料閃爍不定的呈示(exposé)過程中,整個樂章以對位的、守調的、色彩化的方式延伸(比如第一部分的bE小調短句,或指向第二部分開頭的半音移位)。不久就引入了新的材料;這一脈動的、顫抖的樂章在其後的進行中所發生的種種變換,從技術上說,完全由對位組合、轉調和豐富的配器色彩組成。在降E大調交響曲K.543的行板中,迫近的降A小調的陰影甚至在樸實的歌體主題進行當中就能預見。開始主題終止之後引入了新的主題材料作為對立面;最後,錯綜複雜的和聲與明暗法引向夢一般幸福的木管主題(54小節起,125小節起),而在終止短句中,這一主題交給了弦樂,於是最純粹的美伸展開來,如花朵般綻放。在這一樂章中,明暗法的豐富性也是以多種對位疊置手法實現的(如76小節起,87小節起)。如何以精湛的技巧使配器色彩與和聲色彩相互滲透,以至彼此融合,請看從降A小調向B大調的轉調(91小節起),配器上的絲般光澤與等音變換(降A=升G)的精巧靈活融為一體,無與倫比。同一經過句也證明了樂章的有機統一性:等音加主題的強延伸建立在不安的降A小調部分的基礎之上,而此調性早在主題中就已暗示過。在主題最後一次返回(144小節)之前,單簧管在圓號的持續音上奏出魔幻般的阿拉伯風格片段,為樂章的平靜解決作好準備,於是這一情境的轉換就成為整個樂章結構生長的自然結果,在主題組織和色彩兩方面都表現出完美的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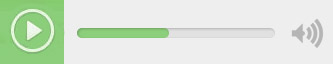
莫扎特:降E大調第39交響曲K.543,第二樂章 稍快的行板,演奏:René Jacobs指揮弗萊堡巴洛克樂團。
莫扎特在慢樂章中發展起來的風格組織手法多種多樣,不勝枚舉。在鋼琴協奏曲中更多強調的常是明暗法而不是對位。木管以自己的插句進入,如K.491,C小調和降A大調的間奏,或K.488,A大調的間奏。最後一部鋼琴協奏曲K.595,「最簡單」的一部,小廣板為一個優美而精巧的降G大調短句所加強,不再藉助於任何明顯的色彩或對位手法。另一方面,在C大調交響曲K.551的行板中,對比是通過堅定的正面衝突而形成的;歌體的主題材料迅速分裂為短小的動機(11小節起),然後被兩個插句打斷,它們之間的撞擊形成了最強的不協和音(19小節起,47小節起);而在這些戲劇性的、野性的激情爆發之上,歌體的旋律又流回來,加上從其自身產生的對位,以豐滿的美感終止。全都很「簡單」。就連著名的不協和插句也只是由簡單的延留音和經過音組成。在這方面,它們使人想起C大調弦樂四重奏K.465那同樣有名的、有爭議的和常遭批評的柔板引子。然而所有這些「簡單」手法所達到的效果,卻是整個十九世紀在發掘了全部手法上的可能,窮盡了一切明暗法的細微變化之後仍未能達到的,正如整個十九世紀再也沒有寫出歌德的「月亮之歌」或「五月之歌」那樣的詩句。當豐富的調性色彩不能使用,比如在奏鳴曲或弦樂四重奏中,作為一種展開的方法,就必須更多地求助於動機分割、對位處理和和聲轉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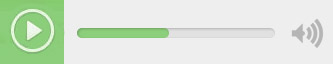
莫扎特:C大調第41交響曲「朱庇特」K.551,第二樂章 如歌的行板,演奏:Bruno Walter指揮哥倫比亞交響樂團。
在G大調弦樂四重奏K.387中,樂章中對位延續的獨立動機直接從行板主題提取而來;但早在8小節起,就可以找到將和聲拓展到降D大調的胚芽,而後(63小節起)它變成了樂章的主要基礎。在小提琴奏鳴曲K.481的柔板中,重點明顯地落在和聲展開的豐富性上;它從降A大調經過F小調到寬廣如歌的降D大調主題,然後經過升C小調和A大調到達升G小調,之後(雖然不是同時在鋼琴與小提琴上)經過等音變換到達降A大調,而在該調上離終止很近的地方有一個非常大膽的經過句。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沒有為對位和調內明暗法提供太多的空間,於是就在和聲展開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A大調小提琴奏鳴曲K.526的行板表現出相似的效果,手法更為謹慎,然而毫不削弱感染力,非常精巧,難以忘懷。弦樂三重奏K.563的降A大調柔板也動用了極豐富的和聲資源,節奏上精巧的細微變化部分地補償了配器明暗法的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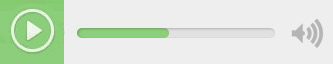
莫扎特:降E大調為弦樂三重奏而作的嬉遊曲K.563,第二樂章 柔板,演奏:Gidon Kremer(小提琴)、Kim Kashkashian(中提琴)、馬友友(大提琴)。
我們對慢樂章主題所作的概括一般地也適用於這些樂章的結構:越晚期的作品,結構越簡單,越克制,越不顯眼。弦樂四重奏K.575和590的慢樂章在「簡單性」方面幾乎不可超越;相反地,四重奏K.465和499的行板樂章在複雜對位的設計上十分豐富,而G小調五重奏K.516的柔板則包含了莫扎特全部作品中所能找到的最大膽的等音疊置(63~64小節)。每個樂章的結構都有高度的獨特性,絕無重複。在多少遵循慣例的外部曲式的框架內,樂思是充盈的。充盈與繁盛不同,它受經濟原則的嚴格約束,去除了一切多餘的成分,從而保持了曲式的統一性。莫扎特從未涉足太遠,至於晚期貝多芬的警句風格,也不曾陷於陳規,如常見於舒伯特的曲式處理。在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中,充盈的樂思竟嘲弄起每一條規則來,以至粉碎了曲式本身;在舒伯特的交響曲和奏鳴曲中,曲式猶如咯咯作響的骨架,勉強撐住奔流不息的樂思;而莫扎特晚期的慢樂章總能在主題內容、展開手法和外部曲式方面達到高度的統一;它們自始至終張馳有度,受制於簡潔性而不那麼顯眼,然而充溢著創意,主題組合無窮無盡;聽眾決不可能把它當作一台沒有彈性的機器,只是為了滿足既定的曲式布局而運轉。這種樂章的展開方式顯然不同於海頓晚期的方式。當然,海頓並不缺乏創意和主題組合的豐富,也不缺乏聲音的美感和曲式的多變;但在他的音樂中我們意識到曲式的存在,而在莫扎特的音樂中,曲式散為一張若隱若現的網,從中彷彿只看到音樂的內容。換一種說法:莫扎特以非凡的功力將形式與內容熔為一體,從而他的樂章只能視為簡潔表達的奇蹟;而在海頓那裡,樂章一開始,我們經常就能預見其進程,或至少在原則上預見。形式嚴整而不落於拘謹,樂思充盈而不流於泛濫,條理明晰而不囿於常規——正是這樣的奇蹟,使莫扎特的慢樂章在一切大師之作中卓然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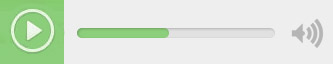
莫扎特:F大調弦樂四重奏K.590,第二樂章 行板 [快板],演奏:The Chilingirian Quartet。
當然,任何語言描述都不可能傳達這一終極內容,它仍是一件秘密,屬於那個創造性的靈魂。真正對莫扎特獲得了理解的人,必將認識到並一再驚嘆於這對稱中蘊藏的豐滿,以及這豐滿本身的對稱。歌德的公式「gepra"gten Form, die lebend sich entwickelt」[「鑄定的形式,鮮活的發展」](他本來指的是另外一個意思)用於莫扎特,就好像專為他寫的一樣;他的「魔鬼」認識到「Gesetz, nach dem er angetreten」[「他若開始必依照法則」],而在鮮活的發展中鑄出更新的形式。在這方面他是獨一無二的——而在純音樂和感情的平衡方面,他也是獨一無二的。與貝多芬作一番簡單比較就可發現,在很多早期的樂章(尤其是1792~1802年的室內樂)中,貝多芬完美地獲得了莫扎特形式方面的流暢與典雅,但其感情內容不能與莫扎特相比;但很快(或許早在鋼琴奏鳴曲Op.2中),貝多芬音樂的感情內容佔據了前台,而音樂絕對物則被推至後台。即使是早期的貝多芬,也沒有獲得完全的對稱,晚期則更不可能。他更多地依靠一種即時的效果來猛烈地衝擊聽眾。在他的所有作品裡,音樂形態的絕對品質與其感情內容的關係(換言之,通常所謂「形式」和「內容」的關係)與莫扎特那裡很不一樣。海頓則又是另外一種情況。海頓作品的感情內容絕不弱於莫扎特(雖然常有人這樣認為),只是表達方式有所不同;或許可以說——以一種慎重的和有所保留的語氣——他的感情內容比較簡單和合乎理性,而莫扎特作品的精神內容則透露出他普羅透斯個性中多樣的、易變的、不可理喻的特性。以音樂絕對物的形式來表現人性,三大師各有其手法,而且彼此決不相同。而只有莫扎特,在表達音樂絕對物的手法中蘊藏了關於終極內容的秘密,它拒絕一切定義而自足存在。
從慢樂章的例子可以見微知著(pars pro toto)。可以對莫扎特所有的樂章,所有的作品作出類似的推演,無論聲樂還是器樂,奏鳴曲快板樂章與迴旋曲還是小步舞曲與序曲。今天我們對莫扎特的生平和背景已經有了精確的了解,直至最詳盡的細節,而他的作品的原始資料也已歷經音樂學批評和文本校訂方面的反覆研究(這當然不意味著所有問題都已解決)。但即使在今天,莫扎特的風格仍未獲得更精確、更全面的定義。Teodor de Wyzewa和Georges de Saint-Foix關於莫扎特寫了一本很好的書,然而我們從中獲得的最有價值的結論仍然更多地局限於他的外部風格與其他大師的比較,而較少地嘗試直接詮釋風格自身的本質。Abert在論莫扎特的兩卷著作的最後寫道:「現在確實應該續寫一本第三卷:關於莫扎特的風格。」就莫扎特的作品對他的時代以及對後代所產生的影響而言,如果有人試圖確定其範圍和本性,就必須著手確定莫扎特的風格中有別於其他大師的特殊品質,並嘗試從這些特殊品質出發推演出莫扎特的影響中的特殊本性。本文應視為朝此目標邁進的一次嘗試。
我們從莫扎特器樂作品的慢樂章入手描述了莫扎特風格的特殊品質,當然這裡還可以增添很多其他的一般特徵與細節。但我們所提到的品質對晚期莫扎特的全部作品是普遍適用的,而且只要謹慎行事,也可以用于衡量早期作品中的「特殊」元素。如果把這些特殊品質接受為莫扎特個人風格的判據,我們就可以部分地闡明莫扎特的影響。他旋律創意方面的精巧明晰使他廣泛揚名於大大小小的聽眾圈子。在對位組合、樂章結構、對位應用、和聲轉調和調性色彩等方面的卓越藝術技巧使他贏得了如海頓和內弗那樣的專家和職業音樂家的讚譽。他的作品中不可理喻的非理性元素,那種「陰暗」的感情內容曾經激怒了不少同時代人,而其技術困難則令其他很多人望而生畏。而他的風格的複合本性,音樂絕對物與精神內容的高度統一,不可思議的駕馭能力,晴空與烏雲的相互交織,「鑄定的形式的鮮活的發展」,卻在浪漫主義者的靈魂中激起了共鳴,使他們把莫扎特當作自己所渴望而無可企及的偶像。然而也正是浪漫主義的時代,為莫扎特的世界聲譽奠定了基礎。
推薦閱讀:
※快步舞的風格特色
※一件衛衣穿出百變風格,選對鞋子是重點!
※都是少女臉,為什麼楊冪光看頭就比趙麗穎重10斤?
※關曉彤的造型問題究竟出在哪?其實她有一種風格很適合大多數女生!
※金科太陽海岸 面積 1200m2 風格 美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