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住在月亮上的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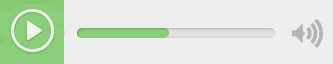
八世紀的一個夜晚,在中國西北的荒野之上,迎著天邊的圓月,一名白衣男子牽一匹瘦馬逆風而行,如在鏡中。
其時胸中漣漪酒意,雄風生,氣壯如依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他寫下了這首樂府: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他是李白。
1300年後的今天,李白詩中的明月依舊照徹今人,而「詩仙」卻好似住進了明月深處,標誌著唐詩精神永遠的顛峰高度與透徹深沉,當中閃爍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之魂。
今人以浪漫主義或詩歌技巧的言辭來讚譽李白竟顯虛浮,倒是當年陪伴李白仗劍江湖行的月亮,以及他詩歌中湧現的各種月亮,構成了一條隱秘的線索,暗示著月亮與詩人的關係,詩歌與人的關係。
「月亮」線索指引讀者走向一個更加真切的李白——這個住在月亮上的詩人。
據對《全唐詩》的不完全統計,李白近千首詩中涉及到月亮的有400多首,「月」的各類意象層出不窮,這些意象不僅是「自然月」的完美再現,而且具備著排山倒海的時間感和超重的宇宙意識,這是李白筆下月亮的超凡脫俗所在,相比「二十四橋明月夜」之類的人工道具,李白的月亮一出現就是八荒六合風起雲湧,在宇宙背景下顯示出神秘優美的闊大性、混沌性與清朗性,他將這三相混合的月光引照塵世,並在空間與時間的進出中切換自如。
李白詩中,月亮不僅有著一種使動狀態(李白以下,詩人們大多將月亮處於「死動」狀態或玩具道具),更有著一種強大而神秘的能動性、主動性(宇宙本性),這二者糾合成李白詩歌的卓絕品質,也昭示出李白與月亮之間的那種親密無間的神合關係。
大唐開元八年(公元720年),李白20歲,出蜀途中寫下了「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這首《峨眉山月歌》寫的是詩人離鄉之感:
我此行即落入時代風雲際會,而故鄉的峨眉山月,你隱去半面憂愁卻又捧出滿懷喜悅來相送。一路上,你窈窕的身影隨著流逝的江水與我不離不棄。夜發清溪向三峽之際,那些山峰阻隔,你開始若即若離,當我到了渝州,我知道已將你永留在故鄉,可心裡依舊暗自盼望你來渝州。別了,峨眉山月,開元八年。
李白行,對故鄉月猶自千呼萬喚。月不隨,似對李白作了讖語之答:「知君用心如明月,何以半隨流水半入塵?」
事實上,頑童性格的李白也並非失去理智,只不過錯將自己的天才當了雄才,渾忘了天下雄才輩出而惟獨一天才難求,自廂願又不得已地陷入塵世泥沙俱下——先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後暗許「猶可帝王師。」(《贈錢征君少陽》),中間還被玄宗「賞」翰林卻留著「待詔」(「詔」即召:召之來、揮之去),後又以皇家體面的客套方式「賜金放還」(「放還」二字盡顯李白月性自白、天性難躬、野性難馴種種瀟洒真趣)。
又,不甘寂寞,致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終,62歲時在湖北游採石璣,身著錦袍,旁若無人醉入江水,捉月,死。(王琦《李太白年譜》),以此結束了自己頑童赤子、詩人遊俠的傳奇生涯,結束了這浪漫又癲狂、愛恨情仇背負寂寞痛苦、夢與醒輪迴交織的一生。
「詩仙」的一生始終盡心,盡氣,儘力,終於盡情、盡才、盡真。是以有現代詩人余光中憐惜語:「酒入愁腸,七分化作月光,餘下三分呼為劍氣,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尋李白》)」。
後人論文化必盛唐,論及詩必言李白,只因李白的「盡」與「真」合一,詩與人合一,人與月合一,作出本真純粹的生命美學行進。
公元757年,56歲的李白正值流放夜郎,昔日腰扎玉帶、布巾風流的少年郎早已不再,那曾被八十高齡的賀知章宰相驚為「謫仙人」的年輕人已不再,某種程度上,他已對「太白金星入懷」的傳說厭倦,悵惘中,李白再憶當年峨眉山月,「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也許離開的並未離開,失去的早已得到,而遠離又未嘗不能是走近的意思?
公元762年,俠客已老,不過兩鬢霜白,忽笑「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痕」的少年任性,忽悟縱有萬古詩才豪情卻桎梏於百年之軀,這時空衝突的大限終是在劫難逃:終與明月相逢。
這條明明滅滅的「月亮」線索全新闡釋了李白之死的真相:他將「天之才」誤作「霸才」標誌著「月之死」,所以當年明月不相送。而當他漸漸明白「仕途」之虛幻,也就是「月之重生」的歷程。
這當中,「月之死」暗示著「李白已(必)死」,而結尾「李白捉月而死」卻標誌著李白與月相逢,與本真的心相逢。
詩人之心本就一剎那可以切入永恆,面對這月不侵水、水不邀月的鏡面,李白旁若無人且傲然一躍,有誰知道他是徹骨的絕望,還是喜逢故人、重返故園的欣然一躍呢?
在李白的詩歌圖譜中,長江、黃河、大海、飛瀑、長風始終此起彼伏,它們構成了唐詩空間里一組獨一無二的宇宙符碼體系,而其間湧現的各款月亮卻在這組平面上樹立起了關於時間、宇宙的縱坐標。
這意味著,平面上自由嬉戲的詩人李白,在這個時空體系中,不僅要承受時間與空間的撕裂之傷,還要對抗時間與空間衝突的雷擊,這個問題始終纏繞著李白的一生:要明月高潔還是要俗世虛榮?要凡俗還是要超脫?
所以,李白的詩歌充溢著莫名傷痛,總是有著「萬古愁」——凡俗終歸不能承受時間之重,也難耐空間之輕。
詩人一方面受到命運的加冕和垂顧,而另一方面又將被命運碾得粉身碎骨,他天生就要承受這種命運。李白曾言「天生我才必有用」,未嘗想此才不僅無法融入空間,更需要千古的時間與千古情懷來解讀。
古來人中龍鳳分三品:一曰仙、二為聖、三稱家,李白以「詩仙」譽世,想來不成「家」都不行。其以月為友,一生都默契著月之軌跡: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幹人(《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李白一生經歷四個女人,開頭和結尾都是宰相的孫女,中間是兩個平民(其中一個看不起他),儘管其為人真情摯性,但到底是否付出過「愛情」卻令人懷疑,因其未曾留下一首顯著有關的愛情詩,而他將兒子起名為「明月奴」,也頗令人費解。
蒼茫雲海間,對一個住在月亮上的詩人而言,他到底愛人還是愛月?凡俗軀住著一顆宇宙遊子的心,他一生能不遠遊么?若無漂泊,他還是李白么?
蒼茫雲海間,但見一輪孤月隨李白遠遊,轉身驚覺,原來這空酒杯、書上塵與心中事早經千古冷。
陶琳:住在文字中的女子
推薦閱讀:
※今天我們為什麼不再紀念詩人顧城?
※詩人佳作 || 慕白:《我是愛你的一個傻子(組詩)》(總第58期)
※才華不等於人品!寫「鋤禾日當午」的大詩人,品性卻差到難以置信!
※胡風及七月派詩人
※詩人為什麼會早逝


